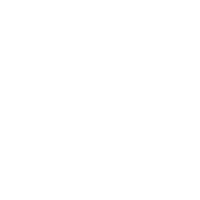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是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民事活动存在困难的根本原因,进而也是宗教财产归属和宗教合法权益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由于宗教活动场所不具备法人资格,导致宗教活动场所的自身管理水平低下,宗教财产所有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各类涉宗教的民商事纠纷难以解决,不少寺庙宫观存在被经营、被承包、被上市的情况,不利于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更不利于宗教团体和宗教的健康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和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明确了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资格和宗教财产权属及其管理途径,为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合法权益提供了行政法规支撑,是立足实践、问题导向的宗教法治战略部署,具有突出的现实针对性。
《民法总则》的创新规定
2017年3月15日,《民法总则》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并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作为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它首次将宗教活动场所纳入法人制度范畴,构建了解决宗教组织从事民事行为和依法保护宗教财产的基础性制度。
法人制度是《民法总则》制定的重点问题。其法人一章的条文数量为45条,居各章之首。不同于《民法通则》按法人的具体形态划分法人类型的思路,《民法总则》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的不同,采取了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的一级分类标准;继而把非营利法人分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机关法人四类;再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捐助法人的一种,最终实现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化。
根据《民法总则》法人分类的规定精神,宗教团体可以登记为社团法人,宗教院校可以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依法经过办理法人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属于“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宗教机构,经依法登记而取得捐助法人资格的法人实体。其性质定位如下:
第一,宗教活动场所经依法登记而成为法人。《民法总则》第58条第一款规定:“法人应当依法成立。”该款确立了法人成立法定原则,类似物权法中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是指法人必须依法成立,不得自行创设法人。之所以确立法人成立法定原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民事主体承担的是无限责任,有限责任只是责任形式的例外。法人却不同,法人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意味着法人的成员、设立人只承担有限责任。第57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第58条第二款规定,“法人应当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法人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是非营利法人。《民法总则》第87条规定:“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宗教场所法人系以宗教活动为目的成立的法人,显然不应具有营利性,否则将有违宗教宗旨和削弱宗教的正常社会功能。《民法总则》将其纳入非营利法人的范畴,这和以往将宗教活动场所理解为“社会组织”“非企业单位”是一脉相承的。根据《民法总则》第95条的规定“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终止时,不得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剩余财产。”这意味着在宗教场所法人终止时,其剩余财产应继续用于宗教事业,而不能向捐助人分配。这将有效遏制宗教活动场所及其捐助人营利动机,使其行为符合法人设立的目的。
第三,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是公益性的捐助法人。《民法总则》明确将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设定为公益性的捐助法人。第92条规定“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人资格。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格。法律、行政法规对宗教活动场所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宗教活动场所设立的目的是开展宗教活动、促进宗教事业发展,有非常明显的公益性,其活动确以信众、宗教团体或其他机构捐助的财产为基础,并不需要会员的参与。
需要指明的是,现行其他立法,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第3条、《信托法》第60条以及《慈善法》第3条都涉及“公益”范畴的法律调整,却均未明确将“宗教”或“宗教活动”纳入公益范围,从而造成法律冲突或者说不协调问题,亟须按照法制统一性立法原则加以修正。
《民法总则》第93条规定:“设立捐助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捐助法人应当设理事会、民主管理组织等决策机构,并设执行机构。理事长等负责人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第94条又细化规定了捐助法人的财产管理规则。综合起来看,上述条款依法确认了宗教活动场所的捐助法人性质,提供了宗教组织依法从事民事行为和保护相关宗教财产的法律路径。
第四,将传统习惯、教义教规作为处理宗教活动场所相关事务的补充性法律渊源。从学理上看,以法律法规为代表的“国家法律”和以教规为代表(还包括道德、社会习俗、乡规民约、组织纪律等)的“社会规范”,形成了人类社会二元调整结构。在《民法通则》时代,行政管理是处理宗教事务的主导思想和方式,《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但在《民法总则》时代,传统习惯被明确纳入民法法源,《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一转变在于:一是在处理有关宗教和宗教事务的民事纠纷时,应当以法律为根本;二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适当引入教规。
新《条例》的制度设计
在《民法总则》关于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的框架基础上,新《条例》第23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符合法人条件的,经所在地宗教团体同意,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法人登记。”第28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内可以经销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宗教出版物。”但作为公益法人,其不得向设立人、出资人分配利润。这就对宗教财产收入的使用予以了限制,即其经营所得收入只能用于宗教目的,如场所的修缮、扩建,日常运转以及向教职人员、工作人员发放工资和生活费用等,不能向设立人、捐助人分配利润。第49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对依法占有的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的财产,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对其他合法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这些规定,改变了原有的回避宗教活动场所是否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的做法,明确宗教活动场所得以法人身份独立开展宗教活动,细化规定了宗教财产权属及其管理途径,为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合法权益提供了行政法规支撑。
第一,进一步明确了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资格。宗教活动场所得以使用其登记注册的法人名义,按照其法人机关的团体意志所形成的决议,独立地从事相应的宗教活动以及相关的日常事务,并且,宗教活动场所得以用该法人名义,接受社会各界捐助人所捐助的财产。同时,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可以将其自有财产和接受捐助所得财产置于法人实体名下,依法能够独立地行使相关财产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知识产权等权利、独立承担和履行民事法律范围内的义务,并在登记机关批准登记的活动范围内从事宗教活动及产生宗教活动场所预期的法律目的。对于其在活动过程中实施的触犯法律行为,依据新《条例》第8章诸条的规定,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第二,确立了我国宗教财产制度的性质与结构,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我国宗教财产制度的法律属性是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新《条例》第52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财产和收入应当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公益慈善事业,不得用于分配”。这对于防止当前存在的宗教商业化倾向意义重大。新《条例》强调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包括其自有财产和收入一律不得用于分配。任何组织或有个人捐资修建宗教活动场所,不享有该宗教活动场所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得以该宗教活动场所获得经济收益。新《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享有的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对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和占有、适用的文物进行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等。出于公益利益需要而征收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应当按照国家房屋征收的有关规定执行,宗教活动场所有权选择货币补偿,或者产权调换或重建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捐赠而享有宗教活动场所的所有权、使用权,也不得从宗教活动场所获取经济收益。宗教组织的财产,只能是捐赠所得,排除将其确认为投资和经营性资产及由此而来的风险。
第三,保护宗教财产,对宗教财产权属进行类型细分。在新《条例》第49条对宗教财产权利作出总括性规定的基础上,第50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占有、使用的文物。”这项规定有现实针对性,有助于防范一些非宗教机构抢庙产、抢寺院土地的事件。过去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在宗教财产归属问题上始终争论不休,新《条例》明确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是宗教主体财产(包括宗教不动产,如寺庙、宫观、教堂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宗教动产,如佛像、法器、经卷、牲畜、宗教自营收入、所受捐赠、知识产权等)的拥有者,并且独立核算、自主管理,可以管理、使用甚至处分财产。从而与宗教团体“两权分离、各行其是”,这有助于作为确定其权属范围的依据,消除内部纷争。
第四,援用传统习惯处理宗教财产和宗教活动场所纠纷。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寺院教职人员的遗产能否由寺院继承并归其所有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僧人遗产纠纷案不少,诸如北京巨赞法师遗产纠纷案、浙江绍兴石佛寺僧人释本耀遗产纠纷案、五台山释含净遗产纠纷案、鞍山千山香岩寺僧人释本愿遗产纠纷案、云南玉溪灵照寺释永修遗产纠纷案等。从审理结果看,个别案件以调解结案,大多数案件将诉争财产判给宗教活动场所所有。这类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宗教教规能否作为法律渊源而存在:僧人的身份特殊,他们一方面是宗教教职人员,必须遵守教规,其权利义务、行为及后果应当按照佛教戒律和丛林清规来处理;另一方面,僧人又是国家公民和法律上的自然人,其法律地位应受国法,特别是《继承法》的约束与保护。按照《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在处理宗教教职人员的遗产继承问题时,不能完全脱离其所属宗教的历史传统和教义教规,佛教内部“一切亡比丘物,尽属四方僧”的传统教规与制度应当作为处理僧人问题的特殊习惯法规范。
建立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制度,对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意义重大。其一,主体资格明确,有助于依法管理宗教,明晰责权利效,提高行政效率,做到行政管理和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各行其是。最大程度上凝聚法治共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成本和损失。其二,组织身份明确,宗教场所心无旁骛地从事宗教事务,以宗教特有的价值服务于社会,其他人无权干涉,为实现高水平的宗教自治提供了保障,便于宗教组织同其他公民和法人组织往来,为扩大交流合作建立了良好基础。其三,诉讼地位明确,有助于场所提起或参与诉讼,依法保护宗教财产,维护各种权益。其四,法人治理结构和民主管理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加强场所内部治理,使场所管理更规范稳定,管理成本大大降低。其五,稳定成熟的涉宗教法律法规,是场所长远发展的基本保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