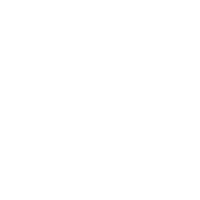历史上的“礼仪之争”,从17世纪中叶争到18世纪中叶 ,持续百年之久。当时,世界上的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都介入其中,最终结果是康熙皇帝下旨禁教。而罗马教廷则宣布中国礼仪违反天主教基本教义,可谓是两败俱伤。
而今时隔几百年,事过境迁,再提到中国礼仪之争,一般人(包括基督徒),也许会一脸茫然,特别是看到欧洲人,为给上帝起一个中文名字而大伤脑筋,为中国的皈依者去祖宗碑墓前烧香或去庙里磕头而大动肝火,有人或许还会莞尔一笑,觉得不值。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西方传教士随着大航海时代到到来,来到远东时,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空前的一场大接触与大碰撞,“礼仪之争”恰恰是中西文明初识时的一个重要回合。对于观察近代早期欧洲或者中国的基本思想走向和基本社会特征,乃至这两个社会权力体系最初的摩擦和冲撞来说,中国礼仪之争是个别是一格的窗口,正因为“中国礼仪之争”背后有如此宽广和深远的思维空间,它已不止是我们广大基督徒应该知道了解的基督教会史或传教史上的知识。它同样对教会今天如何中国化提出思考,带来借鉴。
“中国礼仪之争”的根本起因是基督宗教观念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
一、起因
当“也里可温教”随着元朝的消亡而消失,200多年之后,到了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叩开中国大门,上帝再次来到华夏神州。
耶稣会士的此番叩门并非偶然,既有不寻常的背景,又带着不寻常的力量。
这时的西方已非昔比,它历经文化复兴运动,近代科学文化的晨曦,已驱走中世纪神学蒙昧的漫漫长夜,西方探险家们以“首先拥抱地球”的壮举获得了地理大发现。一方面扩大了世界市场,奏响了殖民掠夺的进行曲,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世界各地文化的联系,推动着西方文明的传播。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在“淘金”的商人赞助结伴下,身负“救人灵魂”的使命,势不可挡地涌向世界各地。这时,他们脑中装的,行囊里带的,从有形到无形的许多东西,已经跟其进入中国的宗教前驱们大不相同。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首先进入了中国。
这时的中国明朝为朱氏:该朝京都的规模宏大,皇家宫阙的宏伟,使之帝国相形见拙。然而,明大帝似缺乏忽必烈那样的气度和胸襟。关起门来做皇帝似乎成了家风,宫门重重就不必说了,后来连四面八方的国门都关起来了。万里海疆实行封禁,不光是为了饿死那些跑到海上去的本国“'穷寇”,也是为了防避来自那个弹丸小邦之地的“倭寇”,以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红毛墓鬼”,而在几乎贴着皇城围墙的地方筑起长城,则主要是为了阻挡北方可怕的鞑靼马队。绝没有想到要给人类留下叹为观止的奇迹。
在当时来说,不管哪一道长城,哪一方国门,都是为了保卫朱家天下。因而,耶稣会士的此番叩门并非轻而易举。号称“东洋宗徒”的沙多略,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就来到广东沿海一个名叫上川的荒芜小岛上,一年多时间,想尽办法也未能踏上大陆一步,最后带着莫大的遗憾死去。面对中国紧闭的国门,有的传教士感叹“磐石啊,磐石,你何时开裂?”
如何使磐石开裂,洋教士们开始琢磨起另外的门路,一个叫罗明坚的人似乎精于此道。他向两广总督等官员多次赠送礼物,三棱镜,自鸣钟等奇物,终于使“看门人”改变了冷漠,傲慢的态度,揖纳洋客了。罗明坚不但被允准留居内地,而且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从澳门携入同人利玛窦,在广东肇庆住了下来。如果说,罗明坚的主要功绩在于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么利玛窦日后在声名,地位和事业上,成为明末来华传教士的首脑人物和重要代表。
利玛窦1582年8月间,自果阿来到澳门,与罗明坚一起学习中文,次年,两人同赴肇庆,大约10年之后,利玛窦在适应策略上迈出具有标志性的一步。即在1592年底之后,在衣着上易僧服为儒服,以便为中国士人接纳。此后数年里,一套完整的适应策略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中逐渐明朗。利玛窦的理想是融合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而建设一种中国----基督宗教式的综合体,使基督宗教真正根植于中国,而摆脱那种被政府视为异端,令民众心怀疑惧的边缘性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除了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关键是为糅合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制定一个可行方案。利玛窦深思熟虑后决定在社会性与道德性因素上沟通两种文化,并最终选择了儒学,而非佛,道作为沟通的平台。这不仅是基于对传教士在中国所要面临的政治形势的仔细考虑,也是出于对中国这几种教义各自内在动力的考虑。利玛窦明白,基督宗教与佛教在教义上存在某种相似性。以致佛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一大竞争者。明确这个方向之后,利玛窦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中国化”要求:
生活方式(带有基本思想和概念的)术语、伦理道德,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礼仪和习俗。
生活方式上的中国化就是接受中国人的举止态度,饮食习惯,睡觉模式,衣着打扮,比如穿士人的丝质长袍,蓄胡须,雇仆人乘轿子以及向有影响的人物赠送厚礼。
伦理道德方面的中国化则表现在利玛窦在中文宣教书和实际讲道中,以儒家的仁、德、道等概念来解释基督宗教的伦理,并且将天主教的戒律和圣经中与儒家伦理有冲突的部分略去。
在术语问题上,利玛窦采用中国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天”或“上帝”指代god/dues;。
在礼仪问题上,利玛窦起初禁止天主教从事祭祖,祭祀礼仪,因为其中有叩头举动,这在天主教徒眼里是膜拜神的行为,但很快他就发现,中国人宁肯拒绝天主教也不愿放弃这些礼仪。
现实困境使他更仔细地观察这类礼仪,发现这类礼仪在中国是有法律规范和身份认同的性质,不执行它们将意味着背弃中国社会,反对它们无异于反对中国政府,同时他又发现,叩头礼也用于对皇帝或父母等生活中的人,因此,既考虑到传教士在中国立足有赖于中国统治阶层的优容,又考虑到叩头行为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礼节性涵义,利玛窦便通融地把祭祖,祭祀礼仪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行为而允许保留。
在生活方式、伦理、术语和礼仪方面顺应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并不意味着利玛窦果然认为中国文化或儒家教义与耶稣会的规定及教义毫不冲突!这一切只是他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所采取的应变之策。因为根据传教士掌握的信息,中国人因为自视为文明发达而排斥一切外来的,新鲜的并自称优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利玛窦传教策略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利用中国古代文献向中国人展示,他们自己的古代宗教与基督教是有相似性的,因此基督宗教不是野蛮的外来事物,同时也提醒中国人,基督宗教因为包含了中西两种古代文明中共有的内容而转移成为中国人接受的宗教,即:至最终清除中国人观念中的异教形态,以基督宗教改造儒学。本着此意图,利玛窦致力于从先秦文献中寻找术语,来表达基督宗教的概念,和依据古书解释中国人的宗教形态及礼仪性质,在术语和礼仪问题上坚持中国化也是相应结果之一。
此外,利玛窦的方法也体现出他真诚尊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态度,正是凭借这种尊重,敏锐的洞察和慎重的取舍,利玛窦才能够被环境接纳,为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发展,奠定基础。但是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方法显得很危险,它可能导致形成一种中国信仰与基督宗教信仰融合的混合物,严重损害天主教信仰力图保持纯洁性与优越性的基本宗旨,所以1610年,利玛窦一去世,在华传教士就因为对其术语和礼仪方面的中国化做法意见不一而拉开了礼仪之争的帷幕。
二 、争论
礼仪之争以耶稣会内部对术语的争议开始,利玛窦以“天”或“上帝”来传达god/deus的概念,是因为他发现中国古籍中也出现过这两个概念,被中国人用来指一个灵魂与人类的统治之主,这个统治主的性质正与天主教及耶稣会所说的真神一样,比如他是一切力量与法律权威的源泉,是道德法律至高的捍卫者,他全知全能,奖善惩恶,而且“天”和“上帝”出现在最多中国人尊崇的古代文献中,也是中国人很熟悉的词语,从策略性角度考虑,它有助于破除中国人中反天主教的偏见,适合天主教徒接受。利玛窦上述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中文宣教书《天主实义》中。
另外,忠、孝两者当中,“孝”对事局的牵涉尤为紧要。孝道在儒家的伦理当中,可谓基下之基,核中之核。由历史悠久的宗法社会孕育出来的这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本位。天、地、君、亲、师,以亲为枢纽,即使忠君也是以孝亲为本。因为“国”乃“家”的扩大,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正是揭示这一关系的。由此便可以理解。从慎终追远意义上体现孝亲的祭祖就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祭祖始终是与教方相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根本上说,中国祭祖并非宗教仪式,而是伦理教化的手段,《礼记·祭统》中很明确地把“祭”视为“教之本”与“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联系起来,可见,祭祖主要是为了教化活人的。
对这一切,耶稣会内部从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其中以1597年到达中国的龙华民为代表的激烈反应。当龙华民接替利玛窦任中国传教区会长时,他曾要求当时罗马教庭视察员吕·巴范济重新审查到利玛窦的主张。但巴范济征求过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及其他人士后,发现他们都支持利玛窦的观点,因此尽管他本人赞成龙华民的看法,却出于维持传教区良好发展态势的考虑而将此问题搁置不议。1617年,龙华民再次向当时的视察员维埃拉写了一篇关于礼仪拜偶像问题的论文。但由于当时传教士中主流观点支持利玛窦,所以没有见效。
1627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底的“嘉定会议”,龙华民的主张并未占上风。
所以1633年,又写文章攻击耶稣会。其《孔子及其教理》被多明我会士闵明我收入《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集》,在马德里出版,在1701年又被摘出来译成法文。以《中国宗教的某些要点》为题,由外方传教会在巴黎刊印,成为18世纪外方传教会反对耶稣会的利器。
1633年来华的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对耶稣会的挑战,才构成了礼仪之争的真正导火索。黎玉范和利安当对在华耶稣会的整套做法都有意见。尤其关注术语问题和礼仪问题。对以中国术语指称上帝,灵魂,天使及其他基督宗教神学术语提出疑问,并指斥耶稣会的容忍教徒祭拜去世的家人,祭祀祖先和孔子,参拜灵牌等。他们在向马尼拉总主教提出指控无果后,黎玉范在1639年以书信方式向耶稣会视察员李玛诺提出意见后,离开中国前往罗马。
1643年,到罗马后,黎玉危觐见教皇马尔维八世,提出他对中国传教区的一些疑问,继而向宣教部递交一份正式报告,请求就报告中涉及内容正确与否做出裁断。提出的十七条问题都是对耶稣会对攻击。
内中有几条比较重要,如:
传教士在给妇女施洗时,是不是可以取消“涂油礼”?
是不是可以准许中国人出百分之三十分利息,靠放债过活的人做基督徒?既做基督徒,是否仍旧可以继续这种职业?
基督徒是否可以捐钱给“迎神赛会”等迷信事情?
国家举行祭祀时,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加此种仪式?
基督徒可否参加祀孔典礼,或其他葬礼。
基督徒是否可称孔子为神?
......
黎玉危对中国人这些行为的描述,有一个突出特点,即用各种宗教性用语来描述,如祭坛,灵魂,跪拜,祈祷,祭品。此举无疑已经判定这些礼仪是偶像崇拜和迷信的,与耶稣会力图将中国礼仪定位为世俗礼仪而极力避免用宗教性术语解释的举动大相径庭。
在此基础上,他又提问,可否以耶稣会所提倡的方式参加这样的礼仪?
于是,当宣教部把这诉状转给圣职部(即宗教裁判所),圣职部召集神学家委员会专门讨论这些问题。当然断定:黎玉范描述的这些迷信礼仪不应被容忍。耶稣会士的举措无疑该受谴责。
1645年9月12日,颁发一道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的禁止命令,并特别强调已在中国和将赴中国的耶稣会士必须遵守该决议。
1648年,禁谕传到中国后引起震动。1651年,耶稣会派卫匡国神甫到罗马去解释。1654年,卫匡国抵达罗马,次年向圣职部提交了一份四个命题的报告。这4个问题都是黎玉范曾提出的有关中国礼仪和术语的问题。但耶稣会以世俗化语言重新表述中国礼仪,否认中国人举行祭祖、祀孔之礼的地方是庙宇。否认摆放供品的桌子是祭坛,否认中国人所行的敬拜仪式里包含宗教意味和祈祷意味。于是,在耶稣会的描述中,中国人的礼仪大体只是世俗性的,政治性的和表达尊敬之情的礼仪。总之,按照耶稣会的解释:这些礼仪仅是出于文明的目的而被设计。
但耶稣会显然回避了一点:这些起初仅是文明性质的礼仪在当今现实中果然不带有宗教或迷信性质吗?而后者正是黎玉范等托钵修士所敏感到的。
关于中国礼仪的原初性质与现实性质的争议,实际就成为未来百年中礼仪之争的一个焦点。
1656年3月23日,圣职部颁发了一道经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批准的部谕,允许中国天主信徒参加卫匡国所描述的祀孔仪式和经利玛窦等人修改后的祭祖仪式。并宣布祭祖和祀孔礼仪可以认为是世俗性和政治性的敬拜。
1669年11月,圣职部颁发一项决议,明确指出1656年与1645年的2道部谕并行不悖。
1664年爆发的杨光先“历狱”事件,大多数在华传教士被禁于广州,并被拘押在同一所房屋中将近5年,这些传教士(包括19名耶稣会士、3名多明我会士、和一名方济各会士)在1667年底到1668年初召开了一个长达40天的广州会议,达成42项条款。第41条便依据1656年的部谕而决定,继续允许祭祖祀孔礼仪,使17世纪最后30年里,中国传教区能够在大体统一的状况下平稳发展。
然而广州会议也埋下一个不安定因素,即就是闵明我,闵明我不能同意广州会议。所以他在1669年12月逃离广州,经澳门返回欧洲,从此致力于驳斥广州会议的决议。
最重要的举动便是出版《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集》,但闵明我似乎没能立刻促使教庭重新考虑整个问题。导致情势急转的关键人物是17世纪末的福建“宗座代收”,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阎当。
阎当1684年便担任实际上的福建“宗座代收”,由于“宗座代收”在理论上被规定为一个传教区的最高宗教领导,所以阎当在1693年3月26日颁发一项彻底否定耶稣会制度的指令。绝对不允许信徒祀孔祭祖,反对传教士把基督的道理去牵合中国古书里的教训,强调基督教所称的god乃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为了要实行这道命令的缘故,用断然手段开除了两名耶稣会信徒,激起耶稣会的反对。
但是,阎当的训令传到欧洲后,却使礼仪之争战火重燃。
1693年底,阎当便派同会的肖莫去罗马递交训令文本和他的一份报告。报告旨在解释1693年训令的内容和依据。
阎当根据自己的调查和了解,在报告中明确表示:
1、中国人的天是指物质性的天空,而无论如何不是天主教的神。
2、中国人绝不是耶苏仑所坚称的那样崇拜唯一真神。中国儒士几乎都是无神论者,孔子更是“无神论之王与无神论博士”。中国皇帝则是当代首席无神论者。
3、祭祖与祀孔礼仪确实是迷信行为等。
1697年,教皇将此交由神学委员会调查研究。
其决议在1704年11月20日才公布。而在此期间,肖莫也将材料给了巴黎主教,巴黎主教则将材料交给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审查,索邦神学院是耶稣会劲敌詹森派教徒的据点,所以他们讨论后在1700年10月18日宣布,反对耶稣会在中国的立场。
这问题既在欧洲闹得满城风雨,教庭便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委员会中没有耶稣会和多明会的人参与,以期公允解决,而此时在中国的耶稣会,适有把“祭祖与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质”的问题去请问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便于1700年11月30日正式宣告,说中国的祭祖祀孔不过是一种尊敬的礼节,纪念其过去的善行,并没有宗教性质。
然而,反对耶稣会的人,便得了一种借口,说关于教会的事,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去请求教外皇帝决定,实在不当。这实是以挑起教皇对耶稣会的恶感。
1704年11月20日,“异端裁判所”经教皇英诺森十二世宣布其禁令,其条文有:
禁止以“天或上帝”称天主。
禁止礼拜堂里悬挂有“青天”字样的匾额。
禁止基督徒祀孔与祭祖。
禁止牌位上有灵或魂等字样。
当教廷代表多罗主教带着这道法令经印度来到中国,1705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后,由于他对耶稣会的成见,康熙帝起初以礼相待,后来这位代表与皇帝的观念站在反对的地位。对于康熙此前所发出的谕旨,不能略为迁就。使宽容优待基督教的康熙帝大大地不悦,乃下逐客令,命其速离京师,多罗不得已离开北京,到达南京。
于是,康熙帝便在1706年12月发出一道圣谕,说明凡传教士非领得朝廷准予传教的印案,及许可,服从中国礼仪的,不准在中国传教。
多罗主教在南京得知这一情况,便宣告了教廷的禁令。康熙因多罗反抗,就把他送到澳门看管起来。当时耶稣会选出两名教士去罗马申说,希望对多罗在南京宣读的1704年的法令有所变更,但罗马教廷又下了一道禁令,重申以前的禁令,必须遵守,并派出代表嘉乐主教往中国调解争执。
1720年12月,嘉乐到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对他非常冷淡,因为过去的争执,本来很不高兴,及至看到教庭的公文更加生气,就在公文上披着这样的话:“欧洲人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礼节”。
嘉乐主教回罗马报告后,教皇便发了一个命令给耶稣会,责备他们没能领导教,服从教会,是对教会的不忠,等等。
时恰巧这时候换了几个教皇,所以礼仪之争搁置。
三、无言的尾声
继承康熙之后的雍正,他本很赞成基督教,所以更固执着康熙的主张。恰巧那时候又另外产出一种争端,即有些基督徒在父母去世时,把父母姓名职衔写在一块白缎上,让教外人叩拜。在福建有些教士并不加以禁阻。北京主教觉得这是违反1742年的教廷禁令的。便通令各教堂,说明向死人叩拜是有罪的,不料,这命令在各教堂发布的时候,引起骚动,甚至有人大喊说“叩头是不是迷信”?
主教选定了这个题目讲道,希望借以安定教友,却不料反而增加了纷扰。因为有些官家或贵族的基督徒,不能容忍这种限制,又再次反抗和争端。教皇鉴于这种纷争长此不息,实非教会之福,便在1775年,把耶稣会解散,这似乎可见教廷当局宁可牺牲在中国的以往工作,也不愿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丝毫妥协,实际上这是罗马教廷和清廷之间,谁都不允许对方将权力凌驾于己方。同时双方对于涉及各自文化核心的问题无法达成共识。
之前,沈澜,杨光先之难平息后,耶稣会在华靠着康熙帝的保护,有五六十年的安宁。现因礼仪之争激恼了康熙,使康熙改变以前的态度,从此历雍正,乾隆,嘉庆以至道光,又遭遇不少挫难,因此,基督教在中国随之逐步消失。
直至鸦片战争以后,1801年马礼逊入华,基督教才再次进入中国。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看到尽管历次反对礼仪的教廷谕旨都乐观地认为服从教皇决议不会阻碍福音传播,但事实却恰恰印证了利玛窦最初的忧虑,礼仪之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礼仪之争所涉及的问题得到解决。今天一些信徒仍受此困惑。其实利玛窦是有耐心和勇气的,他在中国所做的就如同早期教会在欧洲所做的那样,寻找一个具有近似于基督教含义的词语,通过解释和教导而让它们在信徒心中指代确当的基督宗教概念。
可惜16,17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已不是只能在秘密状态下生存的早期教会,它不仅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也自认有着让全世界都服从它的能力,这无疑助长了它的本位主义。
于此同时,16,17世纪的罗马教会刚刚在与新教各教派的对抗中艰难复兴,无论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性,还是为了表明自己与新教派的区别或相对优越性,都有必要严格纪律,强调信仰的纯洁性,也是其原因之一。而这无疑又助长了它的保守主义,这样,礼仪之争也就难免了。
基督教进入中国后,便大力谴责中国人的许多宗教习俗,对山神、河神,佛、道、神祗的崇拜,以及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仪式都被明确界定为迷信。但在面对祭祖和祀孔礼仪时,却遇到了麻烦。祭祖仪式中包括为代表祖先的牌位供奉肉、水果、香料,并在尸体坟墓或牌位前焚香、点蜡、烧纸,然后在家宴中分享供品,这些祭祀是否是宗教活动。
这些礼仪是中国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础,祭拜祖先和过世父母,对中国人而言是孝道的最大表现,而孝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谁若忽视这些礼仪就会不耻于其家族、国人,所以利玛窦认为,人在向先人祭拜时,并没有把牌位当神拜。
“中国礼仪之争”早已落下了帷幕!
这场争论就其直接的涵义而言,是一场有关中国传统敬天,祭祖和祀孔礼仪的宗教属性的讨论。讨论从17世纪持续到18世纪中叶,参加者主要是在华传教士和罗马教廷的神学家。争论的目的在于,判定皈依天父的中国人是否还可继续执行传统祭祀礼仪,而最终结果是以这些礼仪违反天主教基本教义为由拒绝他们。但就在天主教拒绝中国礼仪的同时,天主教也遭到中国社会的拒绝,结果两败俱伤!天主教没能征服中国,中国也拒绝了一次汲取新鲜血液的机会。
其实,《圣经》从原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中文本身,基督教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幕,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惟愿本文能给当今的基督教中国化建设有所思考知借鉴。
本文参考书目:
《中国基督教史纲》王治心著 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礼仪之争》 吴莉苇著 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龙与上帝》 董丛林著 1997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注:本文作者为江苏盐城一基层教会专职传道,2009年毕业于江苏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