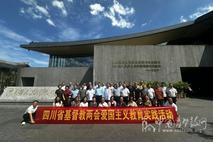在《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结尾,当哪吒和敖丙联手击败无量仙翁,打破仙界的规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场域:“祂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诗40:2)导演借哪吒“挑战规则”的故事,在看似对抗权威的表层叙事之下,实则悄然叩问着人类文明中那亘古不变的命题——罪性与救赎。
一、魔性与人性:在宿命的裂痕中照见原罪的倒影
当银幕上那个身负魔丸,却渴望被认可的孩童奋力奔跑时,我仿佛看见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躁动不安。哪吒脖颈上的乾坤圈,在清冷的月光下泛着金属的光泽,像极了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枷锁——那些深藏于血脉之中,与生俱来的悖逆与暴烈。当元始天尊将灵珠和魔丸分别赋予敖丙和哪吒的那一刹那,我仿佛听见了创世之初那一声叹息般的无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参创2:16-17)上帝所赐予的自由,在人的理解中,似乎竟也埋藏着苦涩的悖论,正如灵珠与魔丸。
申公豹在暗夜里独自舔舐伤口的姿态,令人不禁感到一丝颤栗。他那永远也无法褪去的豹纹,不正像极了我们,试图用虔诚的斗篷来遮掩,却总在午夜梦回时,于梦魇中浮现的那个旧我吗?“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耶13:23)先知于千年前发出的诘问,穿透银幕,重重地落在每一个试图用道德修行来漂白灵魂的修士心上。当我看见陈塘关的百姓们那惊恐的眼神时,突然明白了:我们何尝不是那些高举着火把,恨不得将“魔童”彻底剿灭的暴民?在我们审判他人的那一瞬间,我们都已然成为了该隐的后裔。
李靖夫妇站在屋檐下的剪影,又是多么像无数基督徒父母在恩典与律法之间无助地徘徊挣扎——我们既害怕放纵会成为溺爱的温床,又恐惧那份管教最终会变成另一座高耸入云的巴别塔。当殷夫人说出那句“吒儿只是想要被认同”时,就像是无数破碎的家庭,在无尽的暗夜里发出的呜咽。或许,我们都该重新聆听《箴言》中的细语:“你要用杖责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箴23:14)然而,这根杖,必须是浸透着父母泪水的橄榄枝,是那从十字架上汩汩流出的活泉。
再次重读爱德华兹那篇著名的布道词时,莲花池的倒影也在我的眼前不断荡漾。那位清教徒牧师说,罪是“人心向地狱狂奔的惯性”,而银幕上的魔丸,不过是一个过于可爱的隐喻罢了。导演将罪性如此物化的处理方式,像极了一颗包裹着糖果外衣的苦药,这也让我想起,人们,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会将“悔改”包装成一个自我提升的计划,用以自我安慰。
当哪吒对着苍穹发出那声嘶吼——“魔丸的命就不是命吗?”,我仿佛看见了客西马尼园中,那汗如血滴的人子——祂所承载的,并非某个具象化的“恶”,而是整个人类族群的癌变。
二、莲花与十架:在重生叙事里辨认恩典的指纹
当太乙真人用莲藕为哪吒重塑身躯的那个黎明,在这片古老的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修道院的晨祷钟声也悠扬响起。莲瓣层层舒展开来的慢镜头,让我恍惚间看见了那被天使挪开的墓穴之石。然而,导演让仙人消耗自身修为来换取重生的设定,又何尝不像极了我们,总是妄想用自己的善行来兑换那白白得来的救恩?若是恩典当真能够被挣来,那十字架岂不就成了一桩可耻的买卖?
李靖走向祭坛的背影,在那黎明的微光中被拉得很长,像是要模拟当年耶稣走上各各他的那段苦路。他解下佩剑的姿势是那样的庄重,却让我心痛地想起了那些试图用父爱来填补救赎的缺口的信徒。当他说出那句“他是我儿”时,我仿佛听见了无数父母在上帝面前那无助的哭求。然而,这血脉相连的牺牲,终究不是那为我们这些罪人所流淌的宝血。保罗的话语,像一道光芒刺破了迷雾:“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7-8)
敖丙那破碎的万龙甲,在月光下化作纷纷扬扬的雪花,那些闪着寒光的龙鳞,又多么像我们精心打造的道德铠甲?当他为哪吒撑起冰盾的那一瞬间,我竟想起了多少青少年用那优异的成绩,来换取父母那小心的笑容。导演让这个龙族少年通过自我毁灭来获得救赎,却不知晓真正的自由不是挣脱锁链,而是发现自己早已被爱紧紧镣铐。“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这真理,不是靠修行换来的奖章,而是十字架上那赦免我们的,耀眼的晨星。
哪吒的莲花之躯为何总是让我感到一丝不安?——佛教的轮回与道教的修炼,在银幕上跳着暧昧的舞蹈,却始终缺少那具带着钉痕的复活身体。当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参约20:27)时,祂邀请我们触摸的,不是玄妙的隐喻,而是那道成肉身的伤口。
三、规则与光:在今世图景中等待复活的晨星
这颗星球上,那些在无尽黑雾中苦苦挣扎的百姓,是多么像我们面对死亡时,那无助而又深深的惶恐?无量仙翁以“规则”为名的压迫,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也让人想起了约伯在炉灰中的诘问:“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伯16:21)当哪吒声嘶力竭地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时,又有多少病房中的心电图,正在发出那刺耳的警报?
叛逆是青春的特权。但那安息,才是长子的真正福分。
天劫降临的雷暴之中,哪吒和敖丙并肩作战的瞬间,那座人类一直想要建造的巴别塔,轰然倒塌在了我们记忆的最深处。那些连结着众人的灵珠和魔丸的光芒,又是多么像我们狂热地建造人间天国的野心?然而,真正的恩典,从来不是集体主义的战利品,而是浪子回头时,那父亲奔跑时扬起,带着尘土气息的衣角。当导演让人群手挽着手,想要对抗那既定的“天命”时,我们基督徒多么想告诉他们:真正的救赎(灵魂的得救),不在于那众志成城, 而在于马槽里那孤单啼哭的婴孩。
重读《约伯记》的雨夜,哪吒脚踏风火轮对抗规则的画面,突然有了一丝新的亮光。那个桀骜不驯的少年,又何尝不是现代人那精神肖像?人们高举着存在主义的旗帜,宣称“存在先于本质”,却仍然在每个失眠的深夜,无比渴慕着那份永恒的怀抱。先知耶利米的哀歌,在那雷声中不断回荡:“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17:9) 而基督耶稣在那风暴中安然沉睡的姿态(参可4:38),才是对这混沌最深刻的解答。
四、乾坤圈与蒺藜冠:在束缚中觅得真自由
哪吒与乾坤圈之间的角力,那个用来抑制魔性的金环,又是多么像我们与生俱来的软弱——它不是我们需要拼命挣脱的枷锁,而是通往真正自由的那扇窄门。当那个少年终于学会与这法器共处时,奥古斯丁的智慧也在银幕之上闪烁着光芒:“祢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在你里面安息, 就永远不得安宁。”
敖丙的万龙甲在月光下彻底碎裂,那些叮当作落的鳞片,多么像我们那层层包裹的伪装。多少人,就像穿着那冰冷的铁甲洗澡的人。这,令人想起主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的叹息:“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参太23:25)
真正的释放,不是卸去重担,而是让基督耶稣的轭来代替我们那沉重的铠甲。
还记得小时候,我曾给葡萄藤修剪过枝子。李靖夫妇用乾坤圈守护着哪吒的天真,正如天父用诫命托住我们那不堪一击的脆弱。当殷夫人说出那句“你想做什么娘都陪你”时,让我们想起了爱,这个永恒的主题。
没有约束的爱,只会让心灵像那脱缰的野马般疯狂生长,最终窒息自己的生命。
五、家的神话与永恒家园:在血缘之外遇见圣爱
殷夫人怀抱着哪吒,抵挡那天雷的画面,像极了人们常常会犯的——把家庭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巴力祭坛,顶礼膜拜。当李靖想要以命换命时,仿佛听见了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的第三个试探:“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太4:9)血缘之爱若是成为了终极,那十字架也就会降格成为一种廉价的亲情殉道。
特蕾莎修女毅然离开了阿尔巴尼亚的亲族,来到了遥远的印度。她颈间佩戴的十字架项链,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让那些无助的人们明白了何为基督的爱,何为“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参林后5:17)。当敖丙为了龙族的使命而压抑自己的本性时,他的母亲轻轻地说:爱不是血缘的债务,而是恩典的馈赠。她的微笑,让我想起了主耶穌的话:“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参可3:35)
哪吒那句带着深深遗憾的“唯一遗憾是没和您踢过毽子”,又让我们基督徒想起了另外一句誓言:“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得1:16)
真正的,那永恒的家园,并不在那血缘维系的毽子里,而在那圣爱联结的永恒之中。
六、在银幕的微光里等候真光
哪吒踏着风火轮冲向天际的那一幕,那个东方神话里的少年英雄,何尝不是每一个在恩典的门口徘徊着的现代灵魂?导演用那三头六臂解构着那既定的宿命,却在不经意间印证了保罗的洞见:“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参徒17:28)
在这个解构神圣的后现代的旷野之上,《哪吒之魔童降世》所创造的票房奇迹,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当代人那普遍的属灵饥渴症。那些在黑暗的影厅里微微闪动的泪光,不正像极了奧古斯丁所哀叹的“那颗永远不得安息的心”,正在努力寻找着那可以安息的胸膛吗? 当哪吒最终说出那句“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算”时,我多么想带着他一起去看看各各他山上的那座空墓——因为在那里,最彻底的自我实现,恰恰是向恩典完全的降服。
所有的救赎叙事,都是那复活的主耶稣的倒影,哪怕讲述者并不自知。或许,这就是恩典那奇妙之处——它总能在文化的混沌之中留下那光芒的线索,像是藏在瓦器里的宝贝(参林后4:7),静静等待着那饥渴的人们来辨认真光的痕迹。
当下一个“哪吒”再次在银幕上呐喊时,愿我们能够指着那十字架说:看哪,这才是那真正的“逆天改命”——不是靠那火尖枪劈开混沌,而是让那份爱来刺破死亡的帷幔,让复活的晨光照亮每一个被“规则”诅咒所捆绑的灵魂。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