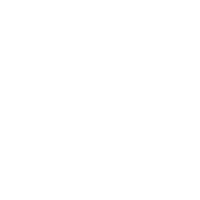门开了,她站在阴影里,像一株许久未浇水的植物。
“你来了。”声音很轻,仿佛随时会断。屋里拉着厚厚的窗帘,午后的阳光被挡在外面,只有缝隙里漏进的一道光,斜斜地切在地板上,像一道伤口。我没有问她好不好。她的不好,写在苍白的脸上,写在凌乱的发间,写在茶几上那杯放了很久、已经凉透的水里。
“他那天说的话,你也听见了。”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像一根刺,扎在这里。”她指了指胸口,“我拔不出来,也不敢用力——怕一拔,整颗心就碎了。”她的目光望向窗外,又好像什么都没看:“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口口声声说爱主的人,会说出那样伤人的话。我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明明没有错,却活得像个罪人。”
角落里,那架钢琴静默着,琴键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我在她对面坐下,没有急着说话。有时候,倾听比言语更有力量。让她把那些压在心底的委屈、愤怒、自我怀疑,都倒出来,这就像清理一个化脓的伤口,总需要先除去腐肉。“你知道吗,”她突然说,“我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打开圣经了。每次想祷告,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我觉得自己不配——一个心里充满苦毒的人,怎么配来到神面前?”
我轻轻握住她冰凉的手:“还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吗?”她微微一怔。“她在正午打水,因为没有人愿意与她同行。她有过五个丈夫,活在指责和非议中。可是耶稣偏偏选在那个最热的正午,坐在井边等她。”我顿了顿,“祂不是去定罪的,祂是去赐予活水的。”她的睫毛轻轻颤动。“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伤口太深就远离。祂靠近一切心碎的人。你觉得自己的心太污秽,不敢给祂看,可祂早就看见了——祂看见的,不是你想隐藏的丑陋,而是祂想要医治的疼痛。”
我起身,走到窗前。“可以吗?”她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哗——”窗帘被拉开了。阳光洪水般涌进来,整个房间瞬间亮了。灰尘在光柱里跳舞,像无数微小的天使。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光刺得眯起眼,下意识地抬手挡了挡。“你看,”我指着窗外那棵树,“它的叶子被虫咬了,枝干也被风雨打折过。可它依然在生长,因为它的根扎在土里,它的生命来自阳光雨露,不来自那些伤害它的东西。”她望着那棵树,久久没有说话。
我回到座位上:“那个伤害你的人,他的话像一阵狂风,可以吹落几片叶子,却伤不了你的根。你的根在哪里?在基督的爱里。这爱,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夺去。”
眼泪终于从她眼角滑落。这不是委屈的泪,是坚冰开始融化的水。“我觉得好累,”她哽咽着,“背着这么重的石头,走了这么久。”“那就放下吧。”我轻声说,“不是原谅他,是释放自己。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主,祂替你担。祂不是说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让阳光温暖着彼此。突然,她站起身,慢慢走向那架钢琴。她伸出手,用指尖轻轻拂过琴键,灰尘像记忆一样被抹去。然后,她坐下来,深吸一口气,双手放在琴键上。第一个音符响起时,有些颤抖,像初生的雏鸟试探着振动翅膀。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渐渐地,旋律连贯起来,是那首《奇异恩典》。“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她的歌声很轻,却像穿透乌云的阳光,一点点驱散房间里的阴霾。弹到副歌时,她的背挺直了,手指也变得有力。阳光照在她脸上,那些泪痕还没有干,却已经在发光。我没有打扰她。我知道,这不是为我弹奏的,这是献给上帝的祭——一个破碎心灵重新整合的赞美。
琴声飘出窗外,融进阳光里。那棵受伤的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应和这迟来的歌声。当她弹完最后一个音符,转过身来时,眼睛是红的,嘴角却带着许久未见的微笑。“谢谢你来看我。”她说。“不是我,”我摇摇头,“是祂让我来的。祂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一直在等你回头看祂一眼。”她望向满室的阳光,轻声说:“是啊,祂一直在等。等我从那个自己建造的牢笼里,走出来。”
有些伤口,需要暴露在光下才能愈合;有些爱,需要再次被记起才能重新流淌。今天,在这间被阳光充满的屋子里,一个灵魂找回了她失落的勇气——不是靠忘记伤害,而是靠记住自己始终被爱。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福建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