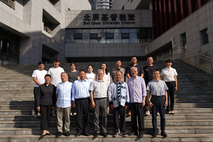近代特别是晚清时期到登州的传教士有一似乎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女传教士比男传教士的数量还多。其实细究起来,也并不奇怪。查近代到登州的外国传教士分别隶属于美国的南部浸信会和北部长老会,而美国这一时期恰恰刚刚兴起女权运动。美国内战促使美国妇女联合起来反对“男权世界强加给妇女的偏见,反对将妇女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她们相信“世界范围内女性的崛起和全世界基督教的传播是同步的”,“相信要实现男女平等必须通过建立在公正的圣经原则上的女权改革来实现”。因此,一些抱持坚定信仰的女传教士们随着海外宣教运动的兴起,毅然远涉重洋,试图“把生活在异国土地上的姐妹纳入这个令人欣喜的大潮中来”。19世纪后半期到登州的女传教士们,怀着这样的理想,积极投身于妇女和儿童工作,开办学校、在妇女中传教,组织妇女开展各种像男人一样的活动,既开辟了中国妇女走上社会的道路,为中国妇女运动的渐次兴起准备了条件,又反过来对美国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构成了19世纪下期“美国社会史上令人惊奇和富有意义的一部分”,促成了“美国生活中妇女第一次多多少少地取得与男子平等地位”的现象。1 因此,广义上说来,女传教士们在登州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比男传教士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在近代来登州的众多女传教士中,慕拉第被誉为她们的杰出代表。
慕拉第(Lottie Moon)1840年出生于美国佛吉尼亚州一个显赫家庭。少年时期家庭条件十分优越,大家庭有八大庄园,800余名奴隶。青年时期在外求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南方第一位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女性,历经美国南北内战,以及战后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和社会的动荡,在寻求人生真谛过程中创办过学校,当过教师。最终她决定到中国做传教士,1873年来到登州。在登州传教、教学四十年(1885-1894年大部分时间在平度),1912年去世。
慕拉第是在有些异乎寻常的情况下去世的。
1894-1895年的日俄战争,严重影响了山东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战前,山东各地每年有大批的劳动力涌入东北,也与东北有大量的港口贸易,劳动力输出和商品贸易对山东经济和百姓生活是极大的补充。战争期间和战后,劳动力输出和商品贸易一度中断,致使“1905到1909年,山东的生活费用上涨了50%”,同时“瘟疫和天花席卷了大半个省,人们常年饥饿”。不仅如此,“1911-1912年革命带来的混乱使事态更严重”,饥荒蔓延,据称灾区“天空的颜色很怪,街道上尸横遍地,农村的母亲们上吊自杀”的比比皆是。慕拉第向美国国内发出了“最后的呼吁”,充满了“为了上帝和人道主义”的惊叫与恳求。然而,这时正值美国南部浸信会本部财政困难,无法援助,慕拉第自己想方设法进行救助,尽到了最大努力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她绝望了。
据说,“从大约1912年中期起,穆拉第小姐开始陷入一种别人称之为不可抑制的忧伤或极严重的忧郁状态。8月,她从上海一家银行取出了为数不多的存款,作为赈灾基金捐献了。在记录本的最后一项上,她写道:‘我祈祷任何传教士都不要象我一样孤单’。她不仅得了悲惨的忧郁症,而且还患有颅骨脓肿,开始象狄考文夫人那样出现幻觉。”
“12月,一位浸信会医生发现她已经决定不再吃东西,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东西了。这是出于她对平度基督教徒的同情而做的决定,因为她相信他们肯定在挨饿。她的同事们决定把她送回国。因此,在一位叫西赛尔-米勒的护士的陪同下,穆拉第小姐被送到一艘12月20日起航的船上。她4天后去世。据米勒小姐说,她去世时似乎正在与‘之前去世的中国朋友们说话’”。
“穆拉第在日本神户港去世,根据日本法律,她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被运到弗吉尼亚州克鲁威镇的浸信会公墓,与弟弟伊萨克埋在一起”。2
慕拉第把痛苦留给了自己,将“芬芳留在了许多本地及外籍人士心底的记忆中”。3
事实上,19世纪下期在登州一批女传教士,像花雅各夫人、倪维思夫人、高第丕夫人、狄考文夫人、梅理士夫人和继室夫人等等,在妇女事业和文化交流方面都作了重要工作,应该说都是那个时代女权运动的先驱,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国际文化交流的楷模。然而,不要说其他女传教士,即便是被美国学者小海亚特誉为山东最著名的三个女传教士的另外两位:高第丕夫人和狄考文夫人,也都没有获得像慕拉第那样的声誉。慕拉第的“名字不仅代表了上百万的美国南浸信会教徒,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她“在一个怀疑圣人的教会中”,“成为公认的圣人”;“在一个被认为充斥着民族仇恨的地方表现出了超越民族的爱。实际上,她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女英雄,从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她超过了所有来华的传教士,甚至也超过了来华的任何美国人”。4
慕拉第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以山东最著名的三位女传教士为例,人们可以认为,高第丕夫人虽然当时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赞誉,但或许由于高第丕和他们夫妇后期脱离了浸信会等原因,她的身后没得到其应该得到的荣誉。狄考文夫人当时也受到熟悉她的中外人士的爱戴,但无论当时或身后,她的声誉都被她的丈夫狄考文过于响亮的名声淹没了,尽管狄考文本人曾多次声称他的成功没有夫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慕拉第之所以享有“女英雄”评价,声誉显赫,或许有一个单身女子的成功与高第丕领导的登州浸信会失败的对比反衬因素在起作用,或许也有人们对她终生未嫁、一心扑在传教事业上、长期孤苦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悲悯、敬佩心情的反应催化的成分。但这些也许有道理,却并非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她是美国人心目中“女权运动的先驱”,是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典范。
今天的人们了解到那时有那么多女性到中国来,或许会以为当时美国国内男女是平等的,女子各方面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地位,其实不然。虽然那时美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高,但美国妇女的地位却与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19世纪上期甚至下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美国,在社会上有很多工作女人是不能做的,例如医生就是禁止女性从事的一项职业,其他即便是传教士工作,19世纪上期妇女也基本上是为男传教士们服务的,不能独立开展工作。总之,妇女虽然可以受教育,但工作只是限定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至于在家庭里,那时的美国,虽然男人尊重妇女的意见,有事“和她们商量,但商量之后如果二者意见不可调和,决定权在男子”,这和中国人自己认为的中国的情形是一样的:在中国的家庭里,有事大多也是“男人女人一起商量,但男人做决定”。5
然而,19世下期,随着大批传教士来华,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是由于最初男传教士们到乡下巡回布道,为了搞好同当地人的关系,也是为了传教事业,更是为了履行在她们看来是上帝派她们来的使命,女传教士们先是担负起了创办和管理男、女学校的任务;继而是挨家逐户走访学生家长和教徒家庭,甚至单独到妇女们中间去传教;随后又承担起救治当地病人的责任,以致创办医院,当起了医生,从而得到了在美国被禁止自由谋取的职业。在登州的花雅各夫人、高第丕夫人、梅理士夫人、狄考文夫人以及慕拉第,都不同程度地涉足了这些领域。
一般说来,“照料病人和给学生们服药多是这些善良女性自然而然的行为,但真正的治病可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她们并不喜欢被迫去给人看病”,因为这在当时的美国也不是女人从事的职业。狄考文夫人就曾经表示:“我不喜欢摆弄药品,我觉得这并不是我所擅长的事情,这使我十分担忧……有时我希望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她们开药,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地回绝所有要药方的人了。”但是,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传教工作的需要迫使她们不得不试着去从事这一工作,因为一方面她们心肠软,经不起人们求情,更要紧的是中国妇女那时不让男人看病,总是希望女传教士们能为他们解除病痛。于是,在传教士队伍中就逐渐出现了大批女医生。对此,连来华的男传教士们最初也是不认同的,如处事一贯温和且说话措辞谨慎的登州长老会负责人梅理士说:“如果是在国内,那我绝不会雇佣一名女医生,甚至是这个称呼都令我反感。但我觉得为了传教工作而让女性接受医护训练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样以来,首先是美国妇女实现了她们在“男性垄断”的美国没有机会实现的愿望,随即又把西方现代医学知识传到了古老的东方中国大地。6
与登州其他女传教士不同或者说更为出色的是,慕拉第曾作为单身妇女,独自深入农村传教,到平度成功地开辟了新布道区,做到了男人们一度做不到的事情。但她的出名或享有巨大声誉,主要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与她独立工作、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思考有关的文字工作。
也许是由于单身生活比别的妇女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许是在高第丕负责登州浸信会期间的差会内部各种矛盾,需要向差会本部乃至美国一些教会媒体做出必要的说明,也许是慕拉第本来就具有这方面的特长,善于深入观察、思考问题,也许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她在来到登州不久就开始写了大量的报告、通信、文章,很多都在美国国内一些报刊上公开发表,有些迅速产生了重大反响。
为慕拉第赢得巨大声誉的不是她的一些关于登州浸信会的工作方面的报告,而是她关于中国社会、她在中国妇女中间的工作、中国妇女生活的变化,以及她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态度等的系列通信和文章。在平度期间,她先后写了几十封这样的“平度来信”。分别发表在美国浸信会本部的《国外差会杂志》(Foreign Mission Journal)、浸信会弗吉尼亚州报《宗教先驱报》(Religious Herald)、乔治亚州的《基督教指南》(Christian Index)上。除了最初的几篇文章介绍了中国的男权、多妻制、迫害女孩等所谓“令人恶心的事”外,大量的是介绍“她与新邻居们的友谊,并认为如果有教会的帮助,那么这种友谊还可以获得‘良好的进步’”。
慕拉第很早就和所工作地方的妇女们打成一片了,她甚至有时候能和中国妇女挤在一铺炕上。随着在中国时间的延长,她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刻了。在发回国内公开发表的通信和文章中,多次反复地谈了她对中国有些问题的看法,也阐明了中美之间的一些差异。
例如,她认为“中美乡村模式的基本差异是中国人群居于村落中进行耕种,而不是以散居的个人农场为单位,这一特点是中美所有社会和政治差异的源头。她认为中国农村与城市相比最引人注目的差异是农村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她认为这是由于帝国的行政控制到了城镇这一级就基本上停止了,使农村的人们可以进行非正式的自我管理”。
又如,她很喜欢她的一些中国朋友,有时在家里一连几天招待朋友一起吃住,虽然对那时中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很不满,但却非常清楚这只是习惯,与心灵无关,总是设法既不得罪朋友又帮助改正不良习惯。登州城里有位官员的姨太太常带着孩子到她家里做客,可这些客人的有些做法在美国人看来是“令人恼火的中国陋习”,如随地吐痰,小孩子们随意乱跑、搬动椅子,甚至站到椅子上,吃东西时把糕点碎渣掉得满地都是,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慕拉第总是温和但又坚持原则地予以纠正。
再如,慕拉第对中国妇女最初是抱着同情、怜悯的心情,憎恨有些男人的不良行为,尽力教妇女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她后来发现,胶东妇女很泼辣,有很多优点,也有一些人不太讲道理,很能骂人,这使她又觉得这样的妇女确实应该有个严厉的婆婆管束。对中国男人,在她看来有些人有可怕的陋习,大部分人生活比较脏乱,但同时她又经过细心观察发现中国男人心灵深处的许多可贵优点和良好品德。
……
总之,慕拉第慢慢地中国化了,晚年她回国休假和朋友们谈起在中国的事情时,总是说“我们那边”如何如何,而不是说中国如何如何。早在1894年她完全回到登州以后,同事就发现她已经“很少跟外国人在一起”了,她最亲近的朋友都是中国人,甚至和一些中国妇女结为“干姊妹”。
正是由于她长期与中国百姓生活在一起,深入细致地观察中国社会各种现象,使她虽有困惑和矛盾,但总体上应该说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有了比同时代的西方人更深切的了解。在她1894年以后写的文章中,有几篇是关于“中国文明”的,这些文章的主旨是要阐明“中国人和西方人彼此误解”的问题,她根据自己的了解告诉美国人说:“我们应记住中国人不是对西方文明惊讶得目瞪口呆的少数野蛮人。相反,当我们自己的祖先还没有脱离野蛮状态时,中国就有了令人景仰的文明。中国人因他们完备的政府组织、古老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而骄傲,因此就难怪中国一直努力避免受到西方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主张“每个传教士都必须愿意向中国社会习俗妥协,努力理解他们的观点并遵循之”。她本人则本着作为中国“一名客人”的身份,在人们需要时“才给他们指明方向”,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灌输什么。为了显示她与当地中国人一样,她尽量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努力和中国农村妇女保持一样的生活水平,甚至为了尊重中国当时的风俗,“她让自己象当地人那样吃饭、睡觉和穿衣”,拒绝和巡回布道的外国男传教士握手,以致引起男传教士的极大不满。
像许多终生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一样,晚年的慕拉第在美国已经没有家了,“她的家族成员散落各地,似乎美国已经变为异乡”。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一名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单身女人,她的忘我精神和工作成就,感动了美国人,她以自己切身体验写的大量通信和文章,给了千千万万美国人以巨大影响。
慕拉第在美国的影响始于她独立在中国人中间传教。早在1876年她的妹妹由于精神和身体原因回国时,南浸信会差会本部仅仅是简单地为其支付了路费了事,而10年后慕拉第本人回国探亲时,佛吉尼亚和乔治亚州的一些妇女则为她们姊妹“集资2400美元帮助这对姐妹寻找合适的住处”。因为这时人们已经通过慕拉第写的大量信和文章了解到她是“一位有智慧、有文化、极具社交天赋的女士”。随着报刊上慕拉第的文章的大量发表,南方浸信会妇女成立了联合会展开工作,虽然一度引起男传教士们的强烈不满,但该联合会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它发起的以慕拉第名义进行的每年的“圣诞捐”,竟然改变了南浸信会的财政不支问题。与此同时,似乎也展开了造神运动,各种关于慕拉第的传记、画册、电影以至语录集成、录音带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减少和消失,反而越来越多。慕拉第在美国几乎就成了神。直至在慕拉第到登州百周年后,美国这种造神运动态势仍有增无减。1973年,“为了纪念穆拉第小姐到达登州100周年,南浸信会确定了当年募捐两千万美金的目标。那一年的宣传活动包括演出一部新电影、发行一套12张的穆拉第摘记卡、出版一本极其吸引人的100周年纪念书籍。这些活动超出了预期目标,多募集到了二百万美金,将所有捐款的总数提高到了259677461美金”。7
截至1980年,有《慕拉第新传》(Catherine B.Allen,The New Lottie Moon Story)第二版面世第六次印刷出版,课件慕拉第在美国影响之一斑。有时间和机会,这部新传应译成中文。至少,该好好通读一遍。
最后说句多余的话。慕拉第出身美国南方奴隶主贵族家庭,但在美国无论那个阶层的的人心中都成了英雄,至今念念不忘纪念她。我们的阶级论,特别是“文革”当中以出身划线害死了难以计数的人,其中大多是社会精英,很多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今天想起来是多么的荒唐!但愿人们的思维不再踏入魔鬼之谷。
注释:
1.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P.66-67.
2.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 pp.122-144.
3.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93.
4.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101.
5. D. MacGillivrary ed.,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1913,P.273.
6.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p.81-86.
7.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p.111-130.


.jpg?w=900)
.jpg?w=172)
.jpg?w=213)
(图:贺卫方的博客).jpg?w=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