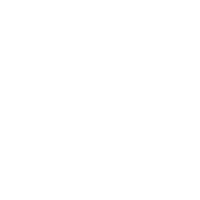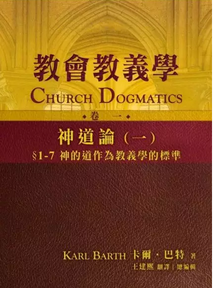【内容摘要】
巴特认为,神学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和反省。如果教会的讲台不忠于圣经的启示,曲解上帝的道,神学就要对教会的宣讲作出引导和修正。今天,教会的宣讲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内部的挑战来自异端,外部的挑战来自文化、意识形态等。余达心教授说:“我们在言说上帝的启示时,有可能因为所用的语言和思想架构而扭曲了上帝的本意;更可怕的是,我们受着时代的意识形态操控而不自知”。[2]
他以“道”为例。“道”这个字在约翰福音中表达为“Logos”.但是“道”也属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类比两者的过程中不对“道”作出教义学上清晰的解释和界定,中国人可能就会以儒家和道家文化的视角来理解“道”。如果教会没有清楚的分辩,穿凿附会,稀里糊涂将两者混为一谈,神学就要让教会的宣讲刹车,作出此“道”不同于彼“道”的宣告。
由此需要提醒的是教会牧者有时用类比文化和福音的方法为了增加某个文化处境中的人对福音的亲切感的心态去传福音时必须慎重处理,如果将文化与福音等同或缩小文化与福音之间的差距,听者就可能无法领略福音真理的奥妙所在,更无法把握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教会不甘人后,生怕落后于人文精神的心思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味迎合人间学问而使听福音的人与救恩失之交臂那是相当遗憾之事。
笔者将在下文中列举三个儒家文化与圣经真理之类比来说明文化与福音虽然有共通、重叠之处。但是文化必须清楚自己的界限和能力范围。在以救赎思维为主导的神学研究和教会宣讲中,文化不能撺掇启示的角色走上神坛变成伪真理、伪启示的冒牌货。
【关键词】儒家文化 基督教 类比 界限 教义学
导 言
英国神学家斯托得(John Stott)牧师曾经指出普世教会的一个现象,“即有增长,但缺少深度”(Growth without Depth)。就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来说,以中国为例,确实是有目共睹的。王艾明教授(Ambrose Wang)引用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指出:“就二十世纪而言,基督教的发展早就令人吃惊地超出先前所有的预期,自1900年以来,基督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宗教在所谓的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已经被大规模地获得了接纳”。[3]
就中国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澎引用《2010年宗教蓝皮书》的统计,中国基督徒有2305万。学术界则普遍认为有5000万以上。虽然,基督徒的人数在中国不断增长,但是根据刘澎教授的观察和分类,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依然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从文化方面来说,基督教在一般中国人眼里依然被视作“洋教”、“西方文化”、“舶来品”。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中国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拥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基督教的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传统儒家文化相比,依然居于次要地位。[4]
另外,著名的儒家学者蒋庆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爆炸式的增长也极为忧虑。他认为,儒家目前最大的敌人就是基督教。2005年,蒋庆在“第一届全国儒家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的论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今中国,基督教凭借着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媒体、教会的力量向中国人传教,据有关人士统计,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近一亿人!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阻止,任其发展,致使今后中国的基督徒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中国就可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主中国,此时再谈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已经来不及。
现在非洲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基督徒,非洲原生态的许多文明已经被基督教文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传统文明已经不可能,故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因此,只有复兴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扩张,才能保住中国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儒教中国”。[5]
在中国政府、新儒家学者和部分中国人看来,中国传统文化都应该受到重视和肯定。但是回顾历史,鸦片战争蒙受的屈辱迫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重估一切传统思想和文化。凡是不符合科学和民主之精神的全部予以抛弃。儒、佛、道三教、伦理纲常等都因为不符合现代思想而遭到无情批判。正如杜维明多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是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的,由于遭到列强欺凌,引发了一连串救亡运动。每一波运动之后,反映的是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怀疑。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从未遭受过如此无情、严厉的批判。而批判中国文化最厉害的不是洋人,而是中国人自己。”[6]
今天,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特别是在经济、军事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民族自尊心不断增长,让许多知识分子开始重新阅读经典。还有一个基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共同的社会学观察,即中国社会正面临“道德崩溃”的危机。“道德崩溃”无论是问责于被功利和应用扭曲的国民教育还是归结为后现代社会或称后工业时代科技社会文化导致的物质主义或个人主义,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正在呼吁在中国社会道德堕落、信仰缺失的窘境下,必须对道德诚信、信仰体系进行重建。而重建工作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所依赖的价值系统则是仁者见仁的事情。
根据庄祖鲲博士将中国知识分子按地区划分(大陆、港台、海外)出的三大阵营,就以大陆学者为例,反传统依然是主流,但是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抱肯定态度的学者。如汤一介、李泽厚等认为,可以从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工作,汤一介认为中国哲学里“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现代意义,可以提示人在发展科技时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避免生态失衡。李泽厚则以人的主体性为首要原则来重新梳理中国哲学思想。[7]
另外一边,刘小枫、刘晓波等人则对中国文化采取反对态度,应该引入西方文化来充实、更新中国文化。但是并不是引进西方文化的“科学”和“民主”,而是引入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精神传统。还有其他一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学者,如刘澎、潘知常、赵林、何光沪、高师宁等都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将会有非常美好的前途和光辉灿烂的远景。不单是就信徒数量,而是从可以挽救社会道德,实现民族复兴这个层面来说。
根据美国神学家理查·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在所著《基督与文化》一书中梳理出的基督徒主张的五种文化观来看,罗马天主教(Catholicism)、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及加尔文(John Calvin)等采取的是“基督改造文化”和“基督超越文化”的立场。[8]
但笔者除了接受这两种立场外,也赞同第三种文化,即基督赞同文化。而这种赞同是指在一般情况下,文化引导人向善,文化不与圣经真理冲突的情况下讲的。从教义学的角度说,因为人的原罪,尽管人类的文化是可以引导人向善的,但还是有缺陷的。加上人本性的堕落,人是无法彻底顺从文化的自我引导的。因此,需要基督的拯救。基督拯救了人,也自然拯救了文化。被基督拯救的人不但能自觉顺从文化的引导,还可以批判文化,必要时纠正文化。因为神写在人心板上的律法,基督徒的生活守则甚至超越了文化对人类的引导而达至一个更加高尚的层面。
因此,只有基督教的超越性才能解答为什么悠久,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不能回避人心灵的矛盾和困局之悲哀。文化的不足在于缺少一个形而上的基础。新儒家认为这个形而上的基础是道德。或者可以理解为“心性”或“人性”。而基督教而坚信,这个形而上的基础是超越性的,即基督的救赎。正是这个恒久不变、四海皆准的“第一原则”才是实践文化或者说成全文化的重要前提。文化有启示性和教育性的功用,唯独没有救赎性。而在保罗看来,基督的救赎(称义)才是实践道德的基础。
笔者将在下文中通过类比基督教与儒家文化试图说明中国中固然包含有崇高的伦理道德,但是文化必然要清楚自己的能力范围,特别重要的是文化必须清楚自身的能力范围的界限。从教义学的角度看,任何企图跨越自身界限跻身于启示前列或与启示等同的行为都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的冲动。作为福音派神学工作者来说,笔者认为大卫·奇勒(David Clark)的“对谈模式”(Dialogical Model)可以引入作为我们对文化采取的比较适宜的态度。[9]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