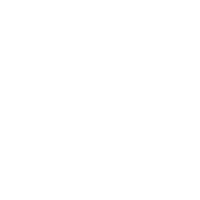经过了漫长的半月连绵阴雨,天空仿佛忘却了季节的轮回,依旧笼罩着一层冬日的寒意。然而,当阳光终于穿透厚厚的云层,洒在上海的上空时,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乘坐火车缓缓驶出这座繁忙的都市,窗外的景色开始悄然变换,仿佛穿越了一个季节的隧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每个星期日的清晨,我都会踏上那条通往九江路上圣三一堂的小路。那是一段心灵的旅程,每一步都踏在信仰的韵律上,每一次礼拜都是与神的对话。随着春风的温柔、夏日的热情、秋叶的静美、冬雪的纯洁,我在圣三一堂的庇护下,感受到了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成长。三月初,我怀着虔诚的心参加了慕道班的学习,那是一段深入了解基督教教义和精神的时光。在牧师的引领下,我学习了圣经的智慧,领悟了信仰的力量,体验了团契的温暖。随着七月的脚步渐近,我接受洗礼的神圣时刻也即将到来。那一刻,我将全身心地沉浸在圣洁的水中,洗去过往的尘埃,迎接新生的自己。我将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这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更是心灵的重生,是对他无限恩典的回应。
在圣三一堂的每一次礼拜、每一次祷告、每一次颂歌中,我都能感受到上帝的爱与平安。我期待着以一名基督徒的身份,继续在这条信仰之路上前行,用我的生活见证信仰的美好,用我的行动传递爱与希望。七月的洗礼,对我而言,将不仅是一个仪式的完成,更是生命旅程中的一个新起点,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期待与憧憬。
去年第一次来这里,是阿文建议的。礼拜开始,管风琴奏乐,唱诗班伴着晨光,从面向东方的大门缓缓走进来。那一刻起,直到礼拜结束,我一直禁不住地流泪。此前多半生,从来没听到过母语的声音可以那么美妙,也从没和这么多同胞在一起,进行这么庄重的仪式。
上海于1843年11月开埠。1847年,英国侨民增多,教友们无法继续在领事馆里做礼拜,于是在九江路建起了简易的教堂。没过几年,旧堂被台风摧毁。1866年,原址重建新堂,三年后落成,成为远东最早、规模最大的圣公会教堂。此后很多年里,圣三一堂的钟塔一直是外滩最高的建筑。
开埠之初,上海只有四条通向外滩的土路。最北面是南京路,即大马路;向南分别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和四马路福州路。
传教士们到上海后,最初驻扎于福州路。所以,福州路最初的名字是Mission Road,即教会路。Mission也是使命的意思,而这条路完成的使命,堪称近代史上的奇迹:最早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最早的现代报纸如《申报》、最早的书店,都曾创办成长于福州路。很多年里,福州路才是这片土地上最具生机、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圣地。当然,和世界上很多人文圣地一样,不能少了风月。福州路的尽头,如今来福士广场那片区域,曾是最有名的红灯区。
福州路和汉口路之间,后来建起了工部局大楼,这是英美租界(公共租界)的最高管理机构。圣三一堂隔汉口路与工部局大楼相邻,正门外的路,最早被称为教堂路,后来改名为江西路。100多年前,这条路上沿街遍布着各国的银行,被誉为“东方华尔街”。
所以,开埠之后的百年当中,圣三一堂一直是租界的政商和宗教活动中心。1893年11月18日,上海工商各界庆祝开埠50周年,举办地就在堂前的花园。
今年二月底做礼拜,布道的尹牧师是上海人,早年家住威海路。他提到50多年前,曾多次和母亲坐49路公交车到外滩,终点就在江西中路九江路。母亲告诉他,这座封起来的红色大房子是礼拜堂,她曾经在这里做过礼拜。
圣三一堂建成后,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升格为上海地区的主座教堂,1949年之前,一直只对英国侨民开放。英国人被赶走之后,教堂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直到1966年8月被彻底关闭。56年之后,于2022年的12月才再次恢复礼拜。
尹牧师说:如今,母亲早已升天,她生前没能再来圣三一堂。而此刻她一定在天堂里看着我,看她的儿子在这里布道。
说到这里,他久久哽咽。
尹牧师祖上就是牧师,到他这里已是第四代。儿子在国外读完大学之后,进了神学院;孙子将来也会考神学院。尹牧师说,他们家里至少会有六代做牧师,而他知道有人家里已有九代做牧师。信神的人,不用担心延续和继承,隔代之间也不会有代沟。
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上海曾经拥有过770座教堂。那时,市区的面积还很小,如今的内环以外都是农田。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应该有很多尖顶和塔楼。清晨和傍晚,到处都会响起钟声与圣乐。
所以,上海是一个蒙恩的城市。而凡是蒙恩的地方,难免都会经历磨难。这未必是神的考验,但蒙恩者会从磨难中获取救赎与重生。在上海,如果不能感受这里的神迹,住多少年,有多少次City Walk,也不会明白她的故事,更无法触及她的灵魂。
鲁迅在上海生活过大约十年,一直住在虹口,他肯定没有来过圣三一堂。我不知他是否去过别的教堂,在信仰方面有过哪些体验。在《天生蛮性》一文里,鲁迅嘲讽:“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把“性灵”和小脚崇拜、王道崇拜相提并论,可见鲁迅对林语堂的“性灵”是不屑一顾的。鲁迅憎恶鬼怪,但他并不理解“性灵”。如果他能多一些去体验和理解,或许会留下不同的文字。
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林语堂曾写道:“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可见,不管鲁迅如何冷言热讽,林语堂始终笑意盈盈。鲁迅写杂文,是要以手中的笔做刀枪;而林语堂写小品文,却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历史证明,怒骂其实比嬉笑更容易被居心不良者利用,这才是更深刻的讽刺。
我无意也无法比较鲁迅和林语堂的人品、学问及成就,更不想去评估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假如我生在他们那个时代,相信我必然属于被鲁迅谩骂的一类,而林语堂肯定不会拒绝我做他的弟兄。去年在阳明山林先生故居的阳台上,望着他曾望过的城市,吃着老阿婆做的厦门炒米粉,我的感觉就像在亲戚家里。
林语堂的父亲是牧师,夫人来自基督教家庭,读书是在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但他自己却是到了晚年才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林语堂学贯中西,他的信仰之旅未必是继承的,或许更是理性的选择。这样的信仰之路,对我来说,更具启示意义。
林语堂毕业的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大学,曾被称为东方哈佛。与圣约翰合作紧密的教会大学,还有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如今,只有东吴大学依然开办于海峡对岸,原来的校址被苏州大学征用。其它几所大学,都早已被撤销了。
东吴大学起源于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而中西书院的创始人是美国人Young John Allen,中文名为林乐知。1859年,23岁的林乐知携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从纽约出发,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航行了210天,才来到上海。此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他和教会、亲友无法联系,也没有任何资金来源,无奈只能在上海卖大米、棉花和保险,后来又当起英文老师和翻译。
从这样的境遇开始,林乐知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最后在上海因病安息主怀。四十七年中,他出版了上百部译著,先后创办了中西书院和中西女中,他主持的《万国公报》深刻影响了清末的维新运动。他被清政府册封过,也被康有为赞颂过,他的学校培养了民国数代英杰,他的故事激励了更多的神的使者。
中西女中最初的校址,位于西藏南路汉口路。迁到忆定盘路(江苏路)之后,原址上建立起沐恩堂,正对着跑马厅,现在名为人民广场。中西书院的旧址在虹口的昆山路,林乐知去世之后,这里建起一座可容纳千人的教堂,名为景林堂。在林乐知的故乡美国乔治亚,有两座以他命名的社区教堂。
林乐知和夫人玛丽在中国又生下八个孩子,1907年去世后,他被葬在了静安公墓。又过了几十年,公墓被铲平,上面建起了静安公园。春天到了,我的朋友老任又要在那里办爵士音乐节。
上海百年,林乐知的弟兄姊妹们成千上万,其中很多人因贫病和教案长眠于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的,除了那些无形的“性灵”,还有最美的建筑、最好的学校和医院。人们若问信仰有什么用,我不知该如何作答。不过你可以去看看,有哪些东西,你希望一直都不要消失。
和国外的教堂不同,圣三一堂没有教友的墓地。我有时想,整个地球,其实都是林乐知这样的不凡者的坟墓: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可能有立柱和碑文,在遥远的国土上也不会被忘记。这些纪念未必是刻在石头上,而是刻在人们的心里。他们曾将勇气视为自由,将自由视为幸福。他们不是偶像,他们应该是榜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上海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