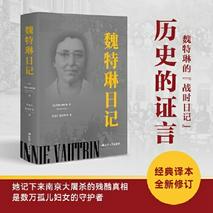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叫张雪岩的基督徒,和他办了一辈子的杂志《田家半月刊》。这不光是个办报纸的事,更是一个信心的故事。他活出了“与哀哭的人同哭”这句话。
一、路走不通了,才找对方向
张雪岩是苦出身。1901年,他生在山东潍县一个穷农家,五岁就没了妈,从小就知道日子有多难。这段经历,让他打心底里认同受苦的老百姓。
17岁那年,为了活下去,也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跑去欧洲当了一名华工。那时候正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国外修路、砍树、挖战壕,亲眼看见了战争有多残酷,也看见了自己国家有多弱,同胞怎么受欺负。这两件事在他心里刻下两个字,救国。回国后,这位热血青年在家门口贴了副对联,“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他要凭自己一个人,闯出一条救国路。
他先去天津一家轮船公司上班,想靠办企业救国。但他看见老板为了自己赚钱,跟外国人勾结,还压榨自己国家的工人。他的理想一下就碎了,气得辞了职。
后来他又去参军,指望当兵报国。他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也在老家拉过队伍。但旧军队里太黑太腐败了,他又一次痛苦失望,最后还是走了。
这两条路都走到了头,把他逼到了绝路上。所有他靠着一腔热血选的路,都走不通。
就在这种叫天天不应的时候,上帝的光照到了他。他年轻时在教会学校听过福音,加上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开导,张雪岩终于明白了。真正的拯救,不是靠钱也不是靠枪,而是要人心归正,生命得改。
他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信了主耶稣,然后进了南京金陵神学院。他把那份救国的热血,全放在了主的祭坛上。一辈子的路,从这里转了向。
二、一份带着土味的杂志,替没人理的人说话
张雪岩从神学院毕业,可没忘了自己是从哪来的。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几亿中国农民。这些人功劳最大,却总“被人们遗忘漠视甚至歧视鄙视”。
他很清楚,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才是中国的根。
1934年8月,他辞掉了青年会总干事的好工作,跟同工孙恩三一起,在济南齐鲁大学校园里,办了一份专门给农民看的《田家半月报》。
这份杂志,从一出生就特别接地气。张雪岩在发刊词里说,“农民是人类最大的恩人。”这句话,决定了杂志的底色和方向。为了让文化不高的人也能看懂,编辑部定了条死规矩。所有文章用的词,都尽量限制在《农民千字文读本》的范围里,而且必须用最简单的大白话写。
对那些写惯了文章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等于要他们完全放下身段,是一种甘心为别人服务的牧者心态。杂志的内容也特别实在,国家大事、种地知识、卫生常识、家庭关系、文艺故事,什么都有。它成了一本真正的“农民教科书”和“好朋友”。
正是因为这种不摆架子的服务,《田家》很快就火了。抗战爆发前,发行量一度有40000多份,在华北的田间地头到处都能看到。
三、战火里的“文化长征”,在绝境里抬头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打了过来,济南眼看就保不住了。《田家》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被迫开始了八年的流亡。这段路,不只是搬家,更是一场信心的“长征”。
1937年10月,报社的人急急忙忙把印刷设备和文件装箱,从济南搬到湖南长沙。可这仗越打越凶,长沙也待不住了。1938年10月,他们只好又往西搬,踏上了去四川成都的苦路。八年抗战,《田家》有七年是在四川过的。
在战争里办杂志,每一步都像踩在钉子上。首先是读者丢了大半,刚从济南搬走时,发行量从快40000份一下掉到2000份都不到,几乎办不下去了。更大的麻烦是钱。杂志本来靠国内外教会捐助,但太平洋战争一打,英美教会的钱就很难进来,甚至断了。同时,大后方物价飞涨,买纸、印刷的钱越来越多,报社常常揭不开锅。张雪岩当时还是齐鲁大学的系主任,他除了教书,几乎把自己的工资全投进了这份看不见回报的事业里,苦苦撑着。
这正是信心最受考验的时候。我们没法想象,在那些快撑不下去的夜里,张雪岩和他的同事们是怎么祷告,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主的。发生奇迹的事情就是人走到头的时候。
《田家》杂志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想出了一些当时很有创意的自救办法。最感人的事是读者们自发了的“一亩运动”和“一元运动”。“一亩运动”是号召读者捐出一亩地的收成。
在那个什么都缺的年代,一亩地的收成、一块钱,对一个穷农民家意味着什么?这就像书中记载:主耶稣称赞过的那个穷寡妇献上的“两个小钱”。正是这无数双沾着泥土、长着老茧的手,献上了自己微小却宝贵的一切。这些奉献汇成一股信心的河,托起了这份风雨飘摇的杂志。杂志不但活了下来,还在1941年8月,把发行量恢复到30000多户。这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算是一个奇迹。
四、抗战时的呐喊,一份杂志的担当
在四川的七年,《田家》杂志的文字跟国家的命运贴得更紧了。张雪岩明确说,战时的口号要变成“人人读田家,个个知爱国”。围绕这个中心,这份基督教刊物,发出了那个时代铿锵有力的声音。
杂志中的“言论”和“新闻”栏目,成了宣传抗战、稳固民心的阵地。张雪岩自己写了很多文章,像《我们要永远纪念双十》、《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他用大白话分析时局,反驳当时政局投降的论调,让待在内陆的农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跟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其中“读者园地”,成了一座连接后方和前线的爱心桥。这个栏目不只刊登读者来信,反映民情,还专门开了“救国捐报告”和“流浪儿童捐报告”,动员读者捐钱捐物。报社常常变成一个抗战捐助的中转站。无数读者通过这里,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物,连同慰问前线士兵的信,一起寄到战场。这份杂志,把散落在乡间的爱国热情,凝聚成了支持抗战的实在力量。
另外“宗教”栏目,更是在苦难里,把基督信仰的真义和爱国精神深深地结合起来。文章反复讲基督教“牺牲爱人”的道理,将之引申为救国爱民的责任。他们还郑重宣告,杂志的立场是“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求解放,为真理做辩护,为自由做斗士”。他们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基督信仰,绝不是躲起来安慰自己,而是敢于面对鲜血,跟受苦的同胞站在一起。
五、“骆驼精神”的见证,一粒麦子睡了
因为常年为国为民奔波,张雪岩累垮了。1950年1月,这位上帝忠心的仆人,在北京安息主怀,才49岁。他这一生,就像一粒麦子,落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苦难的地里。
他没给自己留下什么钱,却留下了一份在战火里活下来,并且深深影响了数万中国家庭的刊物。他也留下了一个基督徒爱国者实实在在的脚印。
《田家半月刊》在抗战时期,不只是基督教在农村办文字事工的宝贵尝试,更是一个在民族危亡时,动员和组织农村老百姓参与抗战的重要工具。它用大白话传播知识和信仰,用实际行动汇聚爱国的力量,为那个苦难的时代,点亮了一盏从乡土来、带着信心的灯。
张雪岩弟兄,和他那种像骆驼一样“默载甚重、任重道远”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篇有力的见证,无需再多解释。
参考资料:
1.《田家半月报》1938~1944年
2.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 (1912—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梁家麟《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天道书楼有限公司1995年版
4.百度百科~张雪岩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