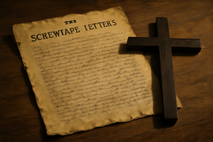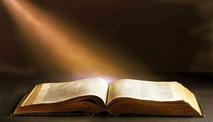莫非:福音时报专栏作家
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一直深信对一个作者来说,阅读永远在写作之先。近来,发现和西方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英雌所见略同”。她在《重点所在》 一书中提到:“阅读先于写作,写作的冲动几乎总是由阅读引起的”。她还坚信:阅读是一种素质,是一种技巧,实践越多,就必然变得越专业。一种有关阅读的意 象从小就在她心中埋伏:那就是维吉尼亚•伍芙在一封信中的名言:“有时我想,天堂就是持续不断、毫无倦意的阅读”。所以,我们是一个悦读者么?我们活得“在地如在天”么?
然而不管写不写作,喜欢不喜欢阅读,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是一本小说。既如此,我们算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呢?武侠、漫画、侦探、爱情、哲理、还是魔幻写实?我们又希望自己是本什么样的书呢?
可知道现在这本书和当年原本希望成为的书,很可能会有出入?原本也许希望是本伟大的爱情小说,结果却成为打来打去、不断过招的武侠小说。也可能原本希望是一本脚踏实地的写实小说,却因一生环境变动,被迫不断寻求思想突围,而成为一本深刻的哲理小说。就像所有的文学作品,小说走向常有其自己的意志和生命,由不得作者的初衷和过度控制。然后,我们该如何审视自己这本书呢?
通常,读小说有五个重要元素:情节、场景、人物、主题和语言。
翻开我们这本书,里面的情节是否已经全被写就了呢?所有过去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是否已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呢?已逝电影导演胡金铨曾经说过:“一个好剧本,必须情节上要合情合理,但结局要在意料之外。”已可推测结局的小说,多半已引不起人有一读的欲望。沧海桑田的日子也许有许多苦衷,却绝对会是一本精采的小说。
我们这本小说是否是以情节为主导呢?什么是以情节为主导?一生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境界随着环境变动,天灾人祸或人事政治变迁而决定?抑或是以故事场景为主导。一生发展和看世界的视野随着生长环境特有的社会文化与地域性而定义:黄土高原、西安古原、滨海渔村、或上海城市?
早期北美《世界日报》的每月话题征文,曾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有一个月话题的征文题目是《命运》。结果港台来美和由大陆出身的作者,作品呈现相当不同的调性。由港台来美的作家写“命运”,大都阳光灿烂,积极进取,强调人定胜天; 一个人的成或不成,和这个人是否能胜过处境有关。由大陆来美的作家则感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只要出身于错误的家庭,一辈子便已被决定、要过担心受怕,甚至牛马不如的日子。
没错,出身背景和走过的时代很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对人生是悲观或乐观,是冲撞还是退缩,也会影响其世界观与人生理念的高低。但是,通常一本好小说不会以情节和场景取胜,而是以人物为主导,英雄造时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才是主导自己这本书的枢纽。所以,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乐观、悲观、依赖、独立、跋扈或柔顺? 因着个人主导,有时在已铺陈出来的情节和场景中,反而打出一记逆反环境的变化球。就如,出身于理想生长环境,却因个性悲观与多愁善感个性,而出现愈走愈低的情节线。出身于困苦环境,却因为独立不服输的个性,而走出永远向上的情节线。同一个时代背景里,虽曾发生文化大革命,影响千千万万,带来一代“伤痕文化”,却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带着伤痕跳楼自杀,或酗酒浇愁郁郁寡欢。个性、价值观,信仰等所组成的“内在组合”,常会使一个人面对变化无常的人世,出现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对待。
正是人的“内在组合”,决定了他是否可以超越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后来拥有的婚姻关系,而走出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局。所以,我们的“内在组合”是贫瘠还是丰富?是坚强还是软弱?是完整还是残缺?我们的“内在组合”多少已掌控了今后的发展如何。
老实说,人生的上半场,我们都不是自己这本书的作者。我们被父母写,被老师写,被社会写,也被后来的配偶或孩子在书写。但现在,想来我们应该比较成熟了,有较坚强,敢于面对不同于世的“内在组合”,是否,可以抓回一些作者的主权呢?但是要写自己这本书,就要有属于个人独特的小说语言。
活到这把年纪,有没有找到一点自己的声音呢?是否有语言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信念?传递待人处世的人生哲学?交待个人的前因后果,以及为何会走至今天?有没有连贯的语言,可以把自己这个人讲清楚,说明白,走到如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此生最大冲突在哪?重要决定怎么作?我们的语言里是否全充满问句?还是也包含叙述解释和分析?
如果一个人活到中年,还讲不清楚自己怎么回事,表示许多人生功课还没有学会,许多感觉思想尚未经整理,从来就没有好好地成长过。
通常小说里应该充满许多问句,但也要有些许答案。如果一路走来,不知问题在哪里,冲突在哪里,却又走了几十年,可以想象这会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想必是一本未曾被人翻开,连自己都未曾书写的一本《无字天书》。面对一生莫大的空白,是否会有很深的遗憾呢?
最后,你这本小说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主题是推动整本小说大方向的主要动力,也可赋予小说多面的丰富意义。若锁定小说主题是《成功》,这本书很可能就会成为一本成功励志型的小说。若锁定主题为《爱情》,也许就成为一本罗曼史小说。若设主题为成名富贵,写出来的很可能是一本争权夺势的权力型小说。反过来说,这一生若一无主题,过一天、算一天,尽随着个性和脾气而胡乱兴风作浪,这本书便自然显得漫无头绪,杂乱无章。
小说主题很重要。它会帮助一个人超脱性格宿命论。什么又是“性格宿命论“呢?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已被其个性给决定了命运。若个性属于优柔寡乱,一生便走不出开阔大格局。若个性是属于悲剧敏感,所作所为便都脱离不了悲剧英雄的路线。但若生命有个大主题,人便会为成就这主题而鞭策自己去成长,去突破,不断地朝着特定的地平线,挥鞭驱马登登登地驰去。
怎么设定一生主题至为重要。对基督徒来说,许多人的生命主题设在《荣神益人》。在这大主题下,又含有许多不同的子题。但这大主题已超乎任何人为能力可以去完成,如果读《天路历程》一书,就会了解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里有多少的难关和诱惑要跨跃。
英国有位名作家却尔斯特顿(G.• K•Chersterton) 曾说过这世上有两种人:当树在风中狂摆时,一种人会想这是风的力量在摇摆树。另外一种人则会想是树的摇动带来了风。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呢?树摇生风?还是风来摇树?
若对人性黑暗的深渊和外界危险的试探有些许了解,便会知道,影响看得见的,往往是那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比什么都实在的力量,这便得一路摸回风的源头来探究。
保罗曾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译: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12章2节) ”若读不同的翻译版本,会发现,耶稣同时是我们信心的创写者(author),也是完成者(finisher)。两千年前,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受死又复活,使得人类的信心历程有个开始。由于耶稣再来的应许,人类才有再走下去的动力,和终极实现的盼望。所以,书写自己这本书就要先设好大主题:跟随耶稣。然后不断寻求各样机会来建造“内在组合”,找出个人独特的声音和语言,活出个人独特的生命色彩。并且这一路的起承转合,全得靠圣灵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仰望神来帮助我们成圣,为主作各样的冲锋陷阵。
如此,我们这本书就相当精采了,就像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里许多云彩样的见证人,虽各有各的软弱和特别,却因着靠神,而行出他们也无从想象的大小突破。
且让我们这本小说成为人物精采,主题超越,而且小说语言很丰富的一本书。让我们努力成为一本耐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