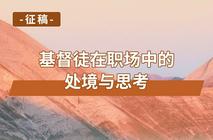圣经说:“犹大家所逃脱的余民,必再向下扎根,往上结果。因为余下的人必从耶路撒冷出来,逃脱的人必从锡安山出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作成这事。”(赛 37:31–32,新译本)
在《旧约》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耶和华上帝以一种缓慢而谦卑的方式更新世界,总是从社会的边缘与底层开始。祂不是借助帝王的权势或祭司的威望,而是通过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来成就祂的计划。例如,上帝带领希伯来这支被奴役的少数民族脱离埃及帝国的枷锁;年轻的大卫以一颗石子击败巨人哥利亚(撒上 17);弥迦预言弥赛亚将出自犹大支派中最微小的宗族(弥 5:1)。这些故事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主题:余民终将成为得胜者。
从边缘出发
先知们是否完全理解这看似矛盾的神圣策略,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学会了在微小、失败与被拒绝的处境中依然坚守使命。通过这样的“筛选”,上帝让真正属于祂的群体显明出来。一个民族或教会整体也许并未全然明白真道,但总有一小群“余民”在每一次试炼之后,依旧传递着复兴的爱与盼望。
这似乎正是上帝的刻意安排。权力往往会扭曲真理,因此上帝选择把真理种植在边缘之地,在那些权势者最不屑一顾、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里。真理对世人而言往往难以承受,但上帝似乎满足于让每个时代都有那么一些人能领悟祂的旨意。先知口中的上帝极其耐心、谦卑,只是匆匆读经的人很难察觉。
被拒绝者的忠心
“余民传统”几乎贯穿整部《圣经》。上帝的信息与使者总是偏离所谓“主流思维”。当我们学会尊重那些被爱却被排斥的局外人时,我们就开始走在神圣之爱的轨迹上,而非停留在只爱同类、只顾私利的本能之爱中。
耶稣也教导同样的真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若非植根于希伯来的“余民神学”,这样的应许几乎无法理解。我们甚至敢说,若人类早早学会这个真理,历史上许多苦难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倘若人们在边缘处寻找真理,而不是在体制荣耀中寻求意义,多少宗教战争、政治迫害、本可避免。
在整部《圣经》中,耶和华始终与那些少数忠信者同工。这迫使以色列民族不断反思他们的救恩神学。正如经上所说:“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番 3:12)这些“余民”成为象征,他们提醒我们,上帝与人同在所需的条件其实非常简单:信靠与谦卑。
那些被称为“蒙拣选”的人,并非因为上帝偏袒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完全信靠那无条件、非惩罚性的神圣之爱。否则我们该如何理解耶稣那句令人震惊的教导:“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太 18:3)这不是天真的比喻,而是揭示了一种深刻的属灵真理,上帝的国属于那些单纯信靠的人。上帝使用所有人,但只有“余民”能自觉地活出托付的使命。上帝在拯救整个历史与人类,但祂需要那些少数忠心跟随的人来活出使命。
“余民”的启示
“余民”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真理:上帝常常借着谦卑的少数群体成就祂的计划,而非依赖权势的多数。这与世人信奉的“多数统治”“权威主导”或“基督教帝国”理念截然不同。
正是通过这些微小的群体,上帝在推动历史的改变。以十九世纪的美国为例:被奴役的黑人群体,比许多白人教会更深刻地理解了福音使人得释放的真义;而当时的白人主流基督教,却在建构排他的帝国信仰体系。这种特权化的白人信仰至今仍在某些文化中延续,充满种族偏见、物质主义与自我中心。上帝当然也爱他们,但他们很少真正活出这爱的自由与喜乐。
在每个教会中,我们总能遇到一些真正接纳自己被爱、被拣选的人。他们仿佛是整个群体保持清醒的支柱。这就是“余民神学”的现实运作方式。余民如同科学中的“临界质量”:在化学反应中,这是触发能量转换所需的最小量;在信仰中,这是激活群体属灵能量的关键。那些看似微弱的少数,常常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边缘力量”:挪亚一家、年幼的大卫、年迈却得子的撒拉和以利沙伯、以及那十二个底层出身的门徒。
若没有这种破除自我的“临界质量”,基督信仰就会蜕变为“公民宗教”——一种以体制、民族或利益为核心的宗教形式。先知们从未屈从这种常态。他们一再揭露权力对真理的扭曲。事实上,他们几乎从未担任官方职务——无论是国王、祭司或长老——却始终在体制之外发出真理的声音。然而,他们并不否认制度的存在价值。耶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祂在圣殿体制之外医治病人,却仍嘱咐他们遵守律法(太 8:4;路 14)。祂公开批评祭司,却未建立对立阵营。这种既持真理、又不陷二元对立的姿态,正是余民的特质。他们带来祝福,而不是咒诅。
当代的“余民”:谁在边缘守望?
放眼今日社会,那些不富有、不出名、甚至身处底层的人,常常背负着不应有的羞耻。人们心照不宣地假设:贫穷、失败一定是个人的错,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聪明,或不属于“正确的群体”。这个世界用财富、地位与效率来丈量人的价值,于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就被轻易归入“无用”的行列。城市的灯火下,多少人带着隐形的羞耻走过,被告知他们是社会机器中可以随时被替换的零件。
然而,圣经却彻底打破了这种逻辑。上帝偏爱不能生育的妇人、被忽视的幼子、为奴的民族。撒拉在绝望中得子,约瑟被卖后成为拯救者,以色列在埃及的苦役中被召为选民。上帝的拣选似乎总是出人意料——他不从显赫之家挑选英雄,而是让“无人要的”成为他救赎计划的器皿。那些“余民”,正承载着被世人忽略的真理:人得以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他被世界肯定多少,而在于他是否仍忠于那位呼召他的主。
这是一条“失败者的传承线”:从撒拉到以色列,从以色列到耶稣。耶稣自己出生在马槽,被称为“拿撒勒人”——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的人;他选择的门徒也大多是渔夫和税吏。上帝的国度从不依赖权势建立,而是从卑微与被弃绝中萌芽。讽刺的是,无论是犹太民族还是后来的基督教世界,其实都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我们更倾向于建立“犹太复国梦”,或在现代版本中,打造辉煌的“基督教帝国”;我们热衷于证明自己强大,却忘了那位救主的十字架是软弱的记号。
在今天,余民仍然存在。他们也许不显眼,不拥有权力,却在默默活出忠信、怜悯与公义的生活。他们可能是一线的医生,在病痛与混乱中守护生命;是贫民区的牧师,在贫乏中播撒盼望;是坚持真理的记者,在谎言之海中守住良知;或是一位无名的祷告者,日夜在上帝面前呼求,为他人守望。世界未必认识他们,但上帝看见他们。
这些余民不是社会的边角料,而是上帝国度的基石。他们用忍耐取代喧嚣,用怜悯取代愤怒,用信靠取代恐惧。他们在黑暗中点燃微光,证明上帝的国并未远离人间。真正的得胜,并非掌握权力的那一刻,而是在一切幻灭之后,仍选择忠心到底。
余民终成得胜者,因为他们从不倚靠自己,而是倚靠那位满有热心的主。那热心正如以赛亚所说,是耶和华亲自成就拯救的力量——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上帝的灵。当世人以为他们已经消失,上帝却在他们的生命里写下新的历史:一部静默的、逆光而行的救赎史。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