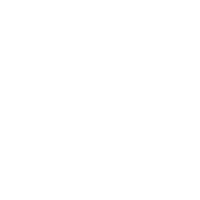笔者被教会出纳拉进一个奉献通知群,自此,每一次弟兄姐妹扫码奉献,我的手机便也会响起叮咚的提示声。
这天晚上,不对,是凌晨一点钟,手机又来一声叮咚,紧接着提示音便告知,有人扫码奉献了十元。于是, 这一声寻常的提示音,让我辗转难眠,这便成了一个不眠之夜。扫码的是一个姐妹,她没有工作,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她的女儿去了深圳打工,她的家公家婆常年患病,需要她常年熬制中药,她的丈夫,在疫情第一年就离开了人世。她便是在殡仪馆送别丈夫时,听到隔壁告别厅的人在唱歌,那是教会弟兄姐妹送别亲人时的祷告与歌唱,感觉不可思议,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后来送遗体到火化车间的时候,大家相遇了。她看到对方送别人群中有一个熟人,事后便细细打听、慢慢了解。就这样,她便成了一个信徒,那张有点皱巴巴的脸,似乎也渐渐有了小小的抚平。
女儿寄回来的钱,大多成了药罐里的根根枝枝和汤锅里的汤汤水水,全都用在了公婆的汤药和一家人的基本生计上;而她对自己,却是省得不能再省。可即便日子过得清贫拮据,但她却也没少奉献,从一开始的两块,到后来的五块,到现在的十块。她本是极聪明的人,用着女儿换下来的手机,一点点摸索着学会上网,学会购物,学会扫码奉献。十元,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可以买一碟肠粉,买一碗肉沫米线,可在大城市的教会里,这十元钱,会不会只是一笔微不足道的零头呢?但我知道于她而言,这十元钱,她已尽力的奉献。失眠的时候,我不免会多想,便忍不住想起两千年前的那个穷寡妇的故事,当富人把一袋袋的银子倒进奉献箱的时候……
那个穷寡妇捏着两枚小钱,指尖被金属硌得发白。那两枚钱是温热的,带着她掌心的汗和她一整天劳作的体温。她躲在柱子后面,看着那些绣着金线的长袍从眼前飘过,看着富人们腰间钱袋沉甸甸地坠着,倒进银库时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一条炫耀的河。
她等所有人都走尽了,才小心翼翼地快步上前。将两枚小钱轻轻投下时,几乎没有什么声响——只是一声极轻的“叮”,像露珠掉在草叶上。但在众人未曾留意的角落,有人看见了 —— 是祂。祂叫住她。她吓得微微一颤,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可祂没有责备,反而对着身边的门徒们学生说:“这妇人投的比众人还多。”
人群瞬间骚动起来,众人满脸不解,那些投下沉甸甸的钱袋的富人更是皱起了眉头。祂平静地解释:“因为他们都是把有余的拿来,而这寡妇,是把自己养生的都投上了。”
两千年后,凌晨一点的提示音还在我耳边响着。那声来自数字时代的“叮咚”,穿过屏幕,穿过黑夜,竟与两千年前那声几乎听不见的“叮”,悄然重合在了一起。原来奉献箱从未空过——穷寡妇的两枚小钱,一直在里面叮当作响,响成如今扫码时的提示音,响成十元钱转入的叮咚声。
这声音很轻,轻得像她熬药时最温吞的那一缕火,轻得像她省下早餐时胃里细微的抽搐。但这声音又很重,重过所有哗啦啦倒下的钱袋。因为这声音里,藏着生命本身的重量,是一个人在深渊里,仍然踮起脚尖,向星空递出的那一点点光。
手机屏幕渐渐暗了下去,我知道,待明日太阳升起时,她依然会早早起来熬药,依然会省下那碟肠粉。但此刻,在无数个这样的深夜里,她的十元钱正穿过数字的河流,抵达某个永恒的地方——在那里,两枚小钱永远不会停止歌唱,永远在歌唱,唱着清贫中的坚守,唱着平凡里的虔诚。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广东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