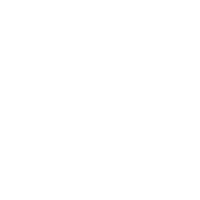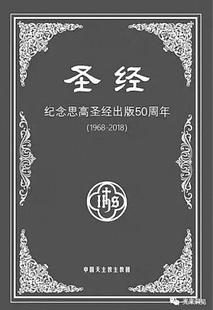摘要:天主教的正义观不同于世俗正义理论,教会认为,它是与仁爱、真理、自由并列的四个社会基本价值之一,它即指对法律制度的遵守,也指一种宗教德行;社会训导的四大原则和正义具有内在关系,原则促成正义的实现,而遵守原则是正义的要求;正义只有在仁爱中才能圆满,但世俗正义观往往只有程序正义,缺少了仁爱等更为优先的美德来做保证。本文在论述了教会正义观的丰富内涵之后,结合中国地方教会的实践和社会现实,对教会的正义观在中国社会落实的两个层面(为教会和为社会的)的已有方式和未来预期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虽然教会社会训导所倡导的正义观对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但也需要教会和信徒的专业化能力,将教义原则在世俗领域现实化,并对教会已有的实践给予指导。
关键词:正义;教会社会训导;仁爱;中国社会
Abstract: The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on justice is different from the secular justice theories, which emphasize the procedural justice. The Catholic Church takes justice as one of the four basic social virtues, and it is not only a juridical concept, but also a religious virtue. There is an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justice and the four principles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s: the principles promote justice to become reality, and justice requests the principles to be followed. Furthermore, the church emphasizes that justice can only be fully fulfilled in and with love and charity. After expounding the rich meaning of Catholic teaching on justice, the discuss focuses on the justice practice by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and suggests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s needed to apply the Catholic teaching on justice into the ecclesiastic practice and Chinese secular society, as it would enlighten and supplement to the established value in China.
Key words: justice;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love; Chinese society
一,讨论正义问题的适切性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1]的不断推进,各种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其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处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因此执政党和政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其奋斗目标,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其前进的目标和动力。[3]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就已经视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等”、“公正” [4]成为执政党的一种承诺和价值目标,如今十九大更是明确把“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系起来,也说出了国人对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的期盼。虽然这四十年来中国逐渐全面开放,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了制度和结构性的变革,改善了法律和政府管理,但是民众不满、义愤的声音此起彼伏。遭遇不公时,很多个人通过上网发声、上访抗议等多种形式争取权益。然而,由于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或者这些民众本身是 “非竞争型弱势化”群体[5],社会要求常常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关注正义如何在当下中国社会现实化无疑是有价值的。
“正义”议题古老而常新。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把正义看作是伦理本性和城邦之本,亚里士多德则把正义和友爱看作是城邦公序良俗的重要保证,“正义”不仅仅是个人德行中的总德(Cardinal Virtue),也是社会制度(城邦政体)的价值归一。在中国儒家伦理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的“仁”和“义”,既是个体立身处世、也是治国理政的至德要义。儒家经典中不乏关于“正义”重要性的论述: “义,人之正路也 ”(《孟子 ·公孙丑上 》, “君子义以为质” (《论语 · 卫灵公 》),“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于利 ” (《论语·里仁》),义利之辩千年不衰。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和已然变化的社会实存,传统的正义思想传统又注入了新的诠释,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它让“正义”成为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重大议题。不过,罗尔斯不再像古典时期那样,将正义放入美德伦理范围来探讨,而是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传统,假设“无知之幕”,将人们放在一种自由、平等、摆脱个体偏见的原初状态,将正义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规范伦理,是社会契约下的一种“公平的规则”,在制度结构的层面来讨论社会正义的这个议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仅在西方学界影响极大,其理论倡导的程序正义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和社会亦有很大的反响,成为本文探讨天主教会推进中国的社会正义实践的重要理论背景。
天主教训导无疑可以说明中国社会以新的视角审视正义,并以更有效的方式实践正义,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生存困境的问题,为社会提供了充满希望的观点。但是问题在于,教会在现代社会已然失去了曾有的道德优势和实现能力。罗尔斯面对以塞亚·伯林的多元价值论难题,提出了“一套恰如其分的平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rights and1iberties)。[6]在这套公共理性框架下、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所提出的制度设想中,宗教和教会提供的只是多元社会中诸多 “合乎理性却又互不相容之完备性学说” 的一种,[7]虽然这种教义对于信徒生活来说具有优先性,但是对于作为信徒的公民而言,这些源于宗教信仰的信念,并不能用来作为其政治主张或支持某个政治原则的论证理由,因为它们并不一定能为其他公民所接受。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不乏教义和现有政策法规相冲突的案例,比如天主教教义和中国社会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张力,持续的张力冲突或给信徒带来信仰淡漠,或造成认识的社会性偏差。与此同时,中国天主教会作为社会团体本身就属于弱势群体,[8]长期蹒跚而行,最近十多年方有投身社会公益之余力,但它和其它社会团体一样,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服务社会的能力都比较薄弱。因此,我们就需要谨慎地避免那种“无效的先知主义”态度,或者“天真的乌托邦主义”,[9]乐观地以为“纲举目张”,各种社会不公可以在社会训导原则的审视下、先知式的批判中土崩瓦解。事实上,教会和社会是两个独立的实存,教会认可世俗的独立性,尊重基于理性和自然律、政治经济以及其它民事领域的运行权限,并愿意与其对话和合作。不过,不少教会人士在仁爱工作的认识上存在误区,只重视个人救赎不关心社会公义,[10]只看重教难致命的见证不重视仁爱工作的见证,[11]或者以为通过国家公共政策或制度改善就可以消除社会不公,让弱势群体最终富起来强起来。因此,教会推进正义的仁爱公益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人们观念的改变。因此,在反思教会的社会训导如何能帮助中国天主教会推进社会正义的实践时,不仅需要有对不同的世俗正义理论的优劣有深刻洞察,看到教会社会训导所倡导的公义原则的启发价值,同时也需要专业化的能力,去将教义原则在世俗领域现实化、对教会已有的实践给予指导。
二.教会关于正义的内涵诠释
天主教会把正义作为社会基本价值之一,与真理、自由和仁爱并列。[12]在圣经中,“正义”一词有时指“伦理德行”,有时指“对法律的遵守”。保禄宗徒不仅把正义与忠信、友爱、良善等美德联系在一起,更把这种品德与遵循福音的信仰生活联系在一起。 “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正如经上所载:‘义人因信德而生活。’”(罗1:17) “真福八端”(玛5:1-12)则是对正义的更高要求,也是对“义人”的最高赏报:神贫的人要得天国、哀恸的人要得安慰、温良的人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要得饱饫、心里洁净的人要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要进天国、为主而受辱骂迫害的人要获得天上丰厚的赏报。这些义人被称为“有福之人”,他们获得了来自天上的赏报,是天主报答了他们的善行,为他们偿还了正义。在圣经中,正义更多地被用于遵守法律规范方面, “天主十诫”(出20:1-17)的每一条都是对正义的要求和维护:敬拜唯一的天主、爱护天主的圣名、守好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近人的妻子和财物。违反天主的诫命就是违反正义,也可以说,正义就是法律和诫命的准绳。
教会不断地进行圣言的反省,根据福音精神解释正义的原则,按照多玛斯·阿奎那的观点,正义是“使各得其所应得的恒常而永久的意志”,[13]教会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审视其道德性。
从主观角度来看,正义是把人当作“位格者”(person)而付出的行动;
从客观角度来看,正义是人应该恒常遵守的道德准则。[14]
这正契合圣经对正义的启示,即从主观角度来说,是忠信于天主和他人的美德;从客观角度来说,是对法律的遵守。
1891年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谕颁布以来,教会的正义观侧重响应现实公益,
一方面坚持信仰的内化原则,鼓励并促进社会继续以正义的精神教育和培育人的良知,
另一方面与时俱进,关心人的处境和外在的正义问题, “正义是一种伦理德行,在于依循恒久和坚定的意愿,给予天主和近人所应得的。对天主,正义又称为 ‘宗教德行’。对人,正义使人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奠定人际关系中的和谐,因而促进人类之间的平等和公益。”[15]
相对于世俗的各种正义观,天主教社会训导所体现的正义观有自己鲜明的特色。2004年宗座正义委员会出版的《教会社会训导汇编》中,在 “教会社会训导原则” 的四原则,即“以人为本原则”、“公共福祉原则”、“辅助原则”和“团结关怀原则”部分,讨论了正义、真理、自由、仁爱这四个社会基本价值,提醒我们这些训导原则与社会基本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原则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是相向的,因为价值是由原则促成的,要实现这些价值,就要求人们必须实践这些基本原则。同样,遵守这四大原则是正义的要求,反过来说,这些原则也会“促成”正义的实现。
四大原则中,“以人为本”最基本,教会的整套社会训导都是从人具有不容侵犯的尊严这一原则而发展出来的。[16]尽管这条原则关注的是人,强调的却是天人关系,因为人有天主的肖像。这种基督徒人类学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而是要有效地实践人权,特别要尊重信仰自由的权利[17],“当一个社会建基于人的超性尊严的时候,它才能成为正义的社会。”[18]
公共福祉原则认为,一切受造物都来自天主,应该公平地惠及全人类,[19] “财物的分配必须有效地回到公共福祉原则,即社会正义的准则”。[20]
团结关怀原则是指人与人、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彼此依靠和相互负责的关系。
这两条原则涉及到社会制度的安排和分配正义,“透过创建或改良法律、市场机制和司法系统,让这 ‘罪恶结构’得以净化,从而转变为 ‘团结关怀结构’”[21],同时也要求政治和社会团体应协调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政府的决策应表达大多数人的意愿,消除某些特权,穷人要得到优先的关爱。
辅助原则则是指基层能做的事情,上级团体就不能越俎代庖,剥夺基层的功能,而只要辅助配合即可,[22]这样也能鼓励个体和社会基层的创造力,从而有利于正义的达成。
三,教会实现正义的途径
如前所述,正义问题是当前执政者和学界的热点问题。人们区分了交往正义、分配正义、法律正义和社会正义,[23]正义关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范畴的正义揭示了不同角度的人的权利和尊严,其中社会正义是其它各种类型或领域正义的统称。教会社会理论和训导原则涉及到所有领域的正义,且与世俗的正义理论并不构成必然冲突。比如教会社会训导的以人为本原则,与新自由主义者们如罗尔斯《正义论》中所倡导 “平等的自由”原则相似,[24]也和马克思主义所畅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25]、当今中国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矛盾。而公共福祉原则与罗尔斯关于公平的正义第二条差异原则,即通过权利和机会平等来保护社会上的地位最不利者[26]非常相似,也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带来异化和阶级压迫的批判、要求改变生产条件的要求有相似性。
这并不是说天主教和世俗思想在关于正义设想和原则没有区别。
虽然教会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反对只追求部分人利益的资本剥削,强调分享和公共利益,但却是一直主张保护私有财产权,这和强调共产主义、剥夺私人财产的做法完全不同;
另外,这条原则和辅助原则、团结原则一样,反对用国家或公益的借口来压制个人尊严抑或剥夺私有财产权,[27]也反对国家集权、官僚主义、福利主义以及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不合理或过度参与。[28]教会捍卫私有财产,并将之看作是自然的权利、是人性尊严的保障;而罗尔斯的理论则把某些特定的财产权(例如生产数据的所有权)移出了基本自由权利的范畴。[29]
更大的区别在于,现代的各种正义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正义的制度和程序,强调的是程序正义,为了达到这种程序化的公平正义,只需要超越各党派、哲学和宗教的“重迭共识”,“不需要借助神学或形而上学的学说来支持正义观念的各种原则,也不需要想象出另一个世界来补偿和纠正正义的两个原则在这个世界所允许的不平等。各种正义观念必须由我们的生活条件来证明其正当性……”。[30] 树立这种程序正义对目标朝向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廉洁政府、建设法制、完善市场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但是,这种中立性原则把正当性放在优于善和美德的绝对地位,导致不少学者的批评。桑德尔批评说,这种程序正义只是补救性的正义,当社会陷入堕落状况时用它来做修理的工作,如果缺少了仁爱或博爱这种更高的、优先的美德来保证,那么就会出现正义也无法弥补的社会衰败。[31]
教会并不否认多样化的经验条件对正义问题的影响,因此,她只提供正义的原则,而不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因为后者需要各地教会团体和信众因地制宜的考虑。[32]考虑到教会与政府是各自独立的机构,社会正义的实现首先是本地教会所在地的政府的职责和管理范围,正义的社会不能由教会来实现, “教会不能、也不应该自己介入实现正义社会的政治角色中,教会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国家。”[33]
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又怎能将自己置身于为正义而奋斗的范围之外?那么教会如何将自己的正义理想变为现实?教宗本笃十六明确地说:应该通过理性思考和灵性力量的唤醒,实现正义,[34]这种灵性的力量就是爱。教会训导中更是说,“在人际关系的各方面,正义都必须被爱大幅度 ‘改正’过来”。[35]这也正是包括桑德尔等社群主义者们对流行正义理论批评时的理解。
作为教会的四枢德之一,仁爱是正义的基础和目标,仁爱修正正义,避免了把正义导向报复和极端,并且引导人们从正义走向人更深的实存,与人本身的尊严相会。[36]今天,实行仁爱仍然是教会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激励人类社会最为有力的方法之一。教会以其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行动,服务弱小,照顾贫穷,通过个人献身、急难救助、赈灾、教育、医疗等等,实践“基督化”的爱与仁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说:“真正的基督化的仁慈,也可以说是人民之间最圆满的 ‘平等’的化身,因此也是最圆满的 ‘公义’的化身。因为实践公义之时,也要达到平等的目的。”[37]
四,大陆天主教会推进正义的实践
教会的正义实践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教会作为社会团体和信徒作为公民,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公正的实践。天主教会发展相比同为“洋教”的基督教是大为逊色的,从上世纪50年代300万信徒[38]到近年的600多万,[39]信徒人数60多年只翻了一倍,无论从神职人员还是宗教场所的数目看都是五大宗教中最少的一个。[40]它面临的既有中国五大宗教的共性问题,也有中国天主教的个性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天主教为了摆脱“洋教”的形象,经过爱国爱教的社会主义改造,曾经开展过所谓“正义的事业”,即反帝爱国运动。[41]1979年之后教会在劫难后复兴,教会为了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做了各种努力。如今教会为了发展,还在为必要的空间而努力。比如最近某地强行 “禁止未成年人进教堂”[42]。接受基督信仰教育是公教孩子的一项权利,也是公教家庭的责任,天主教对家庭宗教教育与中国文化中的家庭本位和伦理优先、强调家教的传统非常一致,古今中外,家教都是人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为公教孩子争取进堂权利这一个案,体现了尊重人之权利的正义要求。又比如大陆的地下教会[43],只因他们选择了“公民不服从”姿态,常有主教神父不知所踪,导致信众无法进行正常的宗教生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重要案例。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包括公民不服从的可能性及必要性,[44] 因此,寻求正义的道路对他们而言是步履维艰、任重道远。
第二层面是教会作为社会团体,为推动整个社会公义而进行的仁爱工作和社会关怀。虽然如今天主教会在中国大陆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较低,但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宗教团体,她的社会关怀和公益服务是有基础的,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其它现代机构无法扮演的角色,比如在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后,天主教会怀着慈悲行哀矜,怀着爱德做善事, 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创办先驱。就拿上海天主教教区而言, 从徐光启时代,上海的天主教会和教友就组织了诸多仁会和圣母善会,恪守哀矜十四端[45],当时中国民间乡绅也有各种“善举”,但天主教的各种善会仁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传统“善举”的动机有很大的不同,善举多是出于善者善报的考虑祸福的行为,但教会的善会则出于更高的博爱动机,是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真正动力。十九世纪上海天主教会先后开设非常有影响的现代科学文教机构,如畲山天文台、徐家汇藏书楼、土山湾孤儿院印书馆、震旦大学、各类中小学校、广慈医院和公济医院等等,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社会服务机构在新政府时代均收归国有,成为新中国公共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革以后恢复宗教自由政策,教会得到恢复重建,在培养神职和修道人之外,教会同时也积极开展社会服务。[46]哪里有教会,社会关怀和服务就不会停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教会共创办的公益慈善机构达259家,其中养老院121家,医院8所,诊所99家,残婴院10家,幼儿园13 所,慈善基金会8个……开展广泛的资助失学儿童,援建希望小学、扶贫救灾,敬老、助残、服务麻风病人,服务艾滋病患者等等服务,同时也为各种自然灾害等捐款。[47]
当前中国天主教会最常见的服务模式中,
第一种是赈灾和义诊。赈灾慈善救济是中国各大宗教中常见的社会服务模式,一方有难八方支持,在各种水旱震雪等自然灾害中,天主教会积极捐钱捐物,捐助医疗物资,提供技术指导等,天主教最早成立的进德公益基金会的重要服务项目就是赈灾。[48]另外,在教堂举行义诊,送诊到乡村,甚至由义诊发展为各类医院诊所。
第二种常见模式是照顾贫弱,服务穷人和贫困人群。不少教区都有助学项目,为本地或外地贫困地区孩童募集资金助其完成学业,援助山区小学。照顾特殊病患、残疾人、孤儿,甚至还有艾滋病患者,麻风病患者。比如辽宁盛京以照顾艾滋病患者、帮助感染者家庭自救等为主要工作。改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存、生活条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引水,修路,通电,医疗诊所,小额信贷、无公害农业,迷你图书馆;救助安老,建立养老院,慰问鳏寡孤独者;照顾城市外来务工人员。
除了前述两种模式,教会还有不少其它服务模式:
比如自愿服务,义务培训外语、堂区服务、支教、环保公益等等;
比如文化交流,不少大城市教会有高水平的教会合唱团, 还有从事理论研究和出版德机构,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有信德文化研究所和出版社,上智研究所,上海光启社等。[49]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慈善的特点是将必要的救济给与职业培育和教育,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或消灭导致贫困的原因,但是天主教会在其曾经的强项——教育和出版事业上受到发展的限制,如果将2013年的统计数字和2017年的九大报告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幼儿园的数量从43所减少到13所,孤儿院和弱智院从16所减少到10所。[50]
五,对国内教会正义实践的展望
实践社会正义是信仰中不能或缺的幅度。为了实现这个使命、在社会中做见证,教会必须维护人性尊严,改善人民福祉,让人有空间发挥其潜能。这是所有地方教会多期望去达成的,只是各地教会实现手段会有不同。我们可以香港天主教会作为参照体系。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主要通过五项工作来实现前述宗旨:
第一,积极响应民生政策,参与社会行动,反对不公义政策,争取政制发展民主化;
第二,关注本地及海外人权状况,提高人权意识;
第三,在教会内提升社会关怀意识,支持堂区内的社会关怀支持组织;
第四,关注大陆事务,
第五,通过出版培育推动。[51]
同为华人教会,香港和大陆教会在推进正义不同的方式和理念,犹如教会上世纪60、70年代对南美解放神学的分歧:当时一部分人强调教会和修会的社会关怀应该从传播福音的角度去处理,避免过于直接地介入社会冲突和政治生活,最多做一些关怀弱势草根的公益关怀。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在社会不平等的地方,教会不仅要高调宣示传福音与关怀被剥削压迫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要勇敢面对和介入争取正义的斗争。[52]香港和大陆教会为实现社会公义所采取的路径显然有类似的差异。
由于大陆特殊的历史和政治环境,教会考虑得更多的是“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化发展道路”,这个“相适应”并不是互相适应,而是让自己的教义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让自己的管理适应中国的国情,是引导自己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当然,宗教团体为了参与公平公正的社会建设,还是可以通过“民主协商”[53]的方式,建言献策,参与政策法规等的决策和执行。除非在严重危害到教会切身利益的前提下(房产被占被拆等),国内教会一般不会采纳抗争民主,通过运用宪法所规定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来行使权利,因为这种街头民主的形式具有不可控性、不利于社会稳定,是不被国家制度所提倡的。另外,由于政治协商主要以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和提案办理协商的方式运作,天主教会代表参与民主协商的范围,原则上是与本宗教团体相关的事务范围,[54]而极少或者不可能就国家政治、法律、财政、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参与发声,而后者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制度保证。 也就是说,教会如果想要在政策制定中参与更多,只能通过拓宽和提升天主教会政协委员在政治协商中的参政议政的能力来实现。就政协这种参政方式而言,政协委员是一种政治待遇,是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产生的。[55]一般而言,政治上靠得住是首要条件,因此,政协委员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表达的首先是党和政府的选拔和认可。教会内部一直就有反对主教神父担任政协代表的声音,认为主教神父的首要工作是传福音的宗教工作,参政议政、推进社会正义是平信徒的责任,教会也有责任去激发平信徒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不过,我们不妨试想,在目前国进民退的当下,如果放弃这个合法的参政议政管道,哪里还能找到更有效的合法途径去介入和监督国家和社会的决策和运作?[56]
改革开放后,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市场机制、公共政策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造成地区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截至2017年底,整个中国仍有3046万贫困人口,[57]其中包括艾滋病村,尘肺病人、留守儿童等这些独特的群体;由于城市人口不在贫困人口统计范围内,城市困难家庭和人口的生存状况被严重低估,城市也不乏失业下岗的居民以及大批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打短工、住棚户、生活困顿不堪、人生没有尊严。这些城乡人口属于绝对贫困群体。用社会学剥夺理论来看,他们处在绝对剥夺的状态。最近十年,权力腐败、阶层分化、利益失衡、司法不公等问题凸显,在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体之外,开始蔓延着普遍的“弱势”感,[58]从高价住房、幼小初学校招生考试、幼儿园虐童案、到雷阳“嫖娼”致死案、谭秦东医生质疑药酒被跨省追捕案……所有的这些现象或事件,激发了不少城市中产、白领乃至金领群体中的无助感,有人称这种现象为 “非竞争性弱势群体”[59]。社会学里称这种现象为“相对剥夺感”,即与参照群体或参照标准相比,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主观心理状态,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表现为愤怒、怨恨、不满,“仇富”、“仇官”、“仇警”、对政府和司法的不信任,整个社会充满戾气。
在帮助这个庞大的贫弱群体的过程中,教会能起到什么作用?政府经济和公共政策的改进着重解决绝对剥夺的问题,但贫弱感并不是单纯由器物层面的匮乏造成的,它涉及到文化、心理或精神等层面的相对剥夺问题,这时宗教信仰可以起到相当重要作用。一项社会调研表明,社会上贫弱群体的怨愤情绪,和现实生活的“权力文化网络”中的尊严感和意义感缺失相关,在这种具体的处境下,“一方面是继续宣传的社会主义平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扩大和资本扩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差别。基督教的平等意识形态与上述二者产生了亲和。”[60]也就是说,客观效果上看,基督教对于贫弱群体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不仅疏导了怨愤,而且提供了新的认知模式。而从教会训导的角度看,从基督徒的主观动机而言,照顾贫弱本身就应是对耶稣诫命的践行,就是信仰的一部分。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25:40)谁怜悯这些弱小者、贫穷者,谁就是敬爱天主、侍奉天主。
希望有一天,当塔吊工人、环卫工人在争取权益,尘肺病人、艾滋病人在勉力求生,留守儿童在烧炭取暖之时,天主教会没有缺席:聆听他们的苦难,照顾他们的需要,用仁爱的服务,去偿还正义的债,[61]最终,通过团结关怀与仁爱,超越世俗的程序正义,提升人性尊严,让信仰之光照亮通向社会正义的道路。正如前教宗本笃十六精辟地指出:“正义并不单纯是人的协议,因为何者为正义,并不是靠实证法(positive law)做最后的认定,而是靠人身份的最深认同。全面性地去看使我们免陷于正义的契约性概念,而能在团结关怀与仁爱的视野中来定位正义。”[62] 这和十九大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 ,推进和实现每个人 、每个群体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包容的理念不矛盾。
参考书目
1. 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教会社会训导汇编》,香港:公教真理学会,2011。
2.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 .
3.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and Auckland: An Image Book Doubleday, 1994.
4. The New Dictionary of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Edited by Judith A. Dwyer, Collegeville, Minnesota: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4.
5. 若望保禄二世,《一百周年》通谕,主教团秘书处编译,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1992。
6. 若望保禄二世,《人类救主》通谕,主教团秘书处编译,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1981。
7. 若望保禄二世,《富于仁慈的天主》通谕,天主教中国主教团秘书处编译,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1981。
8. 若望保禄二世,《生命的福音》,主教团秘书处编译组编译,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1996。
9.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1。
10. 本篤十六,《天主是愛》通諭。
11. 本笃十六,《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牧函》。
12. 本笃十六世,《以正义与和平教育青年》(2012年世界和平文告).
13. 一会一团编印,《中国天主教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专辑》, 北京:一会一团,2016.
14. 一会一团编,《圣神光照中国教会》,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
1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 2018年4月3日。
1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1997年10月。
17. 赵建敏,《天主教社会教义导读》,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10。
18. 《神学大辞典》,辅仁神学著作编委会编,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9。
19. 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0. 多玛斯,《神学大全》(第九册:论智德和义德),胡安德译,台南:碧岳学社,2008。
2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3.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24.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25. 魏尔汉,《企业家的经济作用和社会责任》,雷立柏等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
26.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27. 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万俊人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28. 何夫内尔,《基督宗教社会学说》,宁玉译,雷立柏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9. 万俊人,《义利之间: 现代经济伦理十一讲》,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3年。
30. 邓安庆,《正义伦理与价值秩序:古典实践哲学的思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31. (加)卡里耶,《重读天主教社会训导》,李燕鹏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92。
论文:
32. 李强,警惕非竞争型的弱势化,《人民论坛》34(2010.10):26-27。
33. 许超,正义与公正、公平、平等之关系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2010.2):189-194
34. 陆树程,刘萍,关于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的哲学思考,《浙江学刊》2(2010. 3): 198-203。
35. 许超,正义与公正、公平、平等之关系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2010.4): 189-194。
36. 张国清,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浙江大学学报》6(2013.11):52-62。
37. 麦英健,宗坚固,《富于仁慈的天主》通谕探析,《神思》,86(2010. 8):20-34。
38. 朱晓红,当代中国的天主教社会公益服务:资源,基础和发展空间,《当代宗教研究》,94(2014.1): 1-6。
39. 朱晓红,金鲁贤主教关于社会服务的思想,《中国天主教》182(2016.8):33-37。
40. 乔飞,基督教‘家庭教会”’内部规则及其影响,《民间法》13(2014.5): 225-250。
41. 彭小瑜,天主教社会思想对社会正义的理解,《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2017.4):108-114
42. 田文富,非竞争型弱势化’之权利贫困问题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6(2011.11):57-60
43. 桂华,阶级、‘怨恨’与宗教意识,《文化纵横》1(2013.2):104-108
44. 高夏芳,天主是爱,《神思》86(2010.8):1-8。
45. 曹志,“为未成年人进宗教场所辩护”,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2018-5-14,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8679&from=singlemessage
46. 赵建敏, “当代中国天主教的社会服务”,赵建敏新浪博客,2012-4-12,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261a09010143z2.html
47.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的原则和宗旨,http://hkjp.easyweb.hk。
48. 求是理论网,“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2012, http://www.qstheory.cn/dd/dd2012/xsmz/
49.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宗教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 2017-9-18,
50.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18/c40531-29542397.html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 2018-2-1, http://www.gov.cn/xinwen/2018-02/01/content_5262903.htm
52. 人民日报, “收入差距加大 致‘弱势心理’蔓延”,本文参见东方财富网,2010-11-11,http://money.eastmoney.com/news/1583,20101111104411273.html
[1] “改革开放”是中国政府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推行至今的国家政策,旨在改革落后的体制、扩大对外开放交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2]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一)。
[3] 同上,十九大报告(八)和(前言)。
[4] “公正”(fairness)、“公平”(impartiality)、“正义”(justice)、“公正”(just)、“正当”(right)以及“平等”(equity)等这些词汇的词义和词性在英文中可能有比较明确的界定,“正义”(justice)一词由拉丁文“Jus”演化而来。“Jus”有 “公正”、“正直”、“法律”、“权利”等多种含义。“正义”一方面指人的伦理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指表达一种道德评价。但在中文语义中常常混用,万俊人就说:“在汉语语境中, 正义、公正、公平和公道这些概念几乎可以通用, 它们都表示个人行为的无私、品德的正直和人际关系中相互对待的公平合理。” (万俊人,《义利之间: 现代经济伦理十一讲》,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3,页74)。 不过,目前大陆学者指出,这些概念虽然混用,但是现时需要理清各词使用上的差异,从而在构建和谐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际,避免“歧义和理解偏差……导致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偏离既定轨道, 从而造成利益冲突和社会混乱”(陆树程,刘萍,“关于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的哲学思考”,《浙江学刊》2(2010.3):198-203。一般而言,“正义”是最为根本的伦理德行、是具有绝对善指向概念,其它的概念或多或少从属于正义,或是成为正义内涵的一部分。“公正”是一种事物分配状况的描述,与一定的制度相关,但不必然具有善; “公平”主要关乎人们日常生活的操作层面, 指遵循相同的衡量和对待标准,当公平正义连在一起的时候,“公平成了正义的修饰语”,因为正义并不必然表现为公平,还可以表现为效率和自由; “平等”是一个相对的、比较性的和操作性的概念,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平等含义不同,但正义是自洽的。(可参见许超,“正义与公正、公平、平等之关系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2010.2): 189-194。
[5] “非竞争型弱势化”区别于合法竞争中弱势化现象,是指某些群体被制度设计(比如户籍等制度)排斥在外,是一种制度障碍型的弱势群体。参见李强,“警惕非竞争型的弱势化”,《人民论坛》34(2010.10):26-27。
[6] 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56;以及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页5。本文翻译参见张国清,“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6(2013.11),页52-62。
[7]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页4。
[8] 2014年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中说,天主教人口600万,宗教教职人员8000人,所占人口比例不足0.5%。
[9] 参见魏尔汉,《企业家的经济作用和社会责任》,雷立柏等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页9。
[10] 其实这也是中国基督教新教诸多家庭教会的特征,但进入新千年,在中国兴起的归正宗教会,强调“福音中国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认为神的律法应该在世界的诸多领域施行,重视教会在社会公共事务及文化领域的介入和批判。参见乔飞,“基督教‘家庭教会”’内部规则及其影响”,《民间法》13(2014.5):225-250。
[11] 金鲁贤主教提到有四种认识的误区,看重教难见证、误解仁爱工作就是施舍、以为仁爱就是传福音傅洗、国家政府是慈善工作的主体。参见朱晓红,金鲁贤主教关于社会服务的思想,《中国天主教》182(2016.8):33-37。
[12] 教会认为,所有这些社会价值都是源自人的尊严,人也因这些价值得以真正发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所有人都分享来自同一造物主的同等尊严和价值,因此要求人与人之间必须以尊重和欣赏的态度彼此相待,以正义作为基本的伦理生活准则,保障社会井然有序, “达至个人圆满和社会更具人性的必然途径”。(参见宗座正义和平委员会,《教会社会训导汇编》,(香港:公教真理学会),2011,197号.)
[13] 多玛斯,《神学大全》(第九册:论智德和义德),胡安德译,(台南:碧岳学社,2008),页122。
[14]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 no. 202, p. 117.
[15]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and Auckland: An Image Book Doubleday, 1994), no. 1807, p. 496.
[16]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 no. 107, p. 62.
[17] 参见若望保禄二世,《人类救主》通谕,主教团秘书处编译(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1981),17号,页47-48。
[18]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
[19]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69号。
[20]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 no. 167, p. 95.
[21]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 no. 193, p. 110.
[22] 参见若望保禄二世,《一百周年》通谕,主教团秘书处编译(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1992),48号,页85-86。
[23] “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一词是1840年代首先由天主教思想家提出来的。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社会正义”也成为美国政治和法律哲学的重要主题,而且该词特别频繁地出现在约翰·杜威、罗斯科·庞德和路易斯·布兰德斯的著作中。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国际劳工组织”在自己的宪章序言中明确提出:“和平只能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上”,基于这个观点,有关社会正义的讨论进入了主流法律和学术著作之中。20世纪后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首的一批自由的和保守的思想家反对这个“社会正义”这个概念,认为它什么也没说,或者是说了太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概念在约翰·罗尔斯等哲学家的推崇下,至今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参见何夫内尔,《基督宗教社会学说》,宁玉译,雷立柏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54-58。
[24] 罗尔斯的学说中有两个认为,“处在原初状态中国年的人们将选择两个相当不同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利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个人,尤其是给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礼仪,它们就是正义的。”而这两个原则的作用就是,“一是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的方面,一是制定与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方面。”罗尔斯,《正义论》,页60-61。
[2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里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简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页53。
[26] 罗尔斯关于正义个两条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兼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条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第一个原则就是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条原则就是差别原则或机会均等原则。罗尔斯,《正义论》,页56。
[27] 参见何夫内尔,《基督宗教社会学说》,页28-29。
[28]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 no. 188, pp. 106-107.
[29] 在这点上,罗尔斯认为,为了实现公平的正义,需要对基本自由权中的私有财产权进行特殊的规定,把某些财产权从基本自由权中移除,允许政府通过某些方式比如遗产法赠予法来确保公平。在这点上,有人评价说,他似乎放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石。参见周濂,“哈耶克与罗尔斯论社会正义”,《哲学研究》10(2014.10),页89-99。正如诺齐克批评说,罗尔斯分配正义中的再分配实际上是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将一部分资源转给社会底层弱势者,这里的分配只考虑到接受者的利益,没有考虑到给予者的利益。参见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页183-184。但是,教会将私人财产看作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权利。参见何夫内尔,《基督宗教社会学说》,页28-29,以及页178-184。
[30] 罗尔斯,《正义论》,页456。
[31] 参见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万俊人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页39-40。
[32]保禄六世说:“这要由各地信友团体对其所在国家的特殊情况加以客观分析,并在福音中天主圣言的光照下了解这种情况和教会社会训导中的思考原则、判断准绳及行动指南。”保禄六世,《八十周年》通谕,4号。
[33] 教宗本笃十六,《天主是爱》通谕,28号。也可参见其《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牧函》,4号。
[34] 同上。
[35]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5), no. 206, p. 118.
[36] 麦英健,宗坚固,《富于仁慈的天主》通谕探析,《神思》,86(2010. 8), 页29。
[37] 若望保禄二世,《富于仁慈的天主》,14号。
[38] 参见王文成,“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第一届代表会议开幕词”,《圣神光照中国教会》,页59。
[39] 参见马英林,“坚持中国化方向开创中国天主教爱国爱教事业新局面”,《中国天主教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专辑》,一会一团编印,2016年,18页。这个发展速度,比起基督教将近50倍的增长,实在是相去甚远,基督教50年代人口大约为70-100万,97年为1000万,2018年为3800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7年10月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和2018年4月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
[40] 其实,还可以推出,天主教信众人数也是最少的。目前佛教教职人员约22.2万,寺院3.35万座,道教教职人员4万余人,道观9000余座,伊斯兰教教职人员5.7万与人,清真寺3.5万余处,信教人口2000多万,基督教教职人员约5.7万余人,教堂和聚会点约6万处,信教人口3800多万人,而天主教教职人员约0.8万人,教堂和活动堂点为6000余处,信徒约600万。由于佛道教人数难以统计,如果按照白皮书资料全国信教公民有2亿,那么佛教和道教人口约为1亿3千多万。见 2018年4月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
[41]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第一届代表会议,那时决议上宣称,反帝爱国运动是一项“正义的事业”, 从这种提法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参见一会一团编,《圣神光照中国教会》,(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页79。
[42] 最早流传在公众媒体的类似公告出现2018年4月8日,发布者为河南省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之后河南各地政府宗教主管部门和教育局纷纷联署发布禁令,如某教育部门的公开信http://www.zmwgy.cn/xxzx/ppjs/sxxy/2018/04/13/1443006221.html。具体也可参见曹志,“为未成年人进宗教场所辩护”,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8679&from=singlemessage,2018-5-14登入。
[43] 是指改革开放之后不愿意加入爱国会组织,不愿意以加入爱国会为条件在政府登记的天主教团体。
[44] 如果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论,公民不服从是 “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本着良心的却又是政治的反抗法律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以这种方式行动,人们表达共同体的多数人的正义感,并宣称:按照他们经过考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没有受到尊重”(罗尔斯,《正义论》,页320);而按照这个定义,公民不服从理论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因为选择公民不服从的主体只能诉诸普遍的、与个体或所在团体无特殊关联的共同价值,而不能将公民自身(所在团体或宗教)特殊价值观念带入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苏格拉底,他以自己的死提出了公民不服从的理由,即以法律为至尊的精神。如果以此理解,地下教会采取的公民不服从姿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道义的弱势,国内不少学者对于地下教会的做法也不抱同情态度,认为他们对爱国的理解不够。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核心价值构建的起点是由国家政体决定的现实的生活方式,如此以来,爱国只能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不仅我们的言论具有违宪的可能,而且所提出的所谓核心价值可能即不核心,也不具有实质的规范性”,见邓安庆,《正义伦理与价值秩序:古典实践哲学的思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页79。
但是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来理解,公共权利通过法律运用到社会,这个法律运用是通过服务多数人的不完美的程序来完成,这个程序正义在运作的过程中可能偏离价值,不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么,公民不服从就是对这个不再合理或不再合法的共同认可的程序的反抗,并通过公共领域的这种反抗来修正和完善政治系统。参见杨礼银,“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199.html,2018-5-14登入。和中国的现状相结合,通过六十多年来的发展,教会的现实已然发生巨大变化,“反帝爱国”的任务已经完成,神职人员完成本地化,有悖教会教义原则的机构会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是否还需要强制人们参与,制度和政策规定的修正是否可能?而对于这些选择不服从的弱小的地下教会,他们自从选择了不参与之后,就被从制度和政策上剥夺了诸多的合法公民权利,比如不少地下神父主教没有户口、不能申领护照、不能自由旅行。 当然,无论罗尔斯还是哈贝马斯的理论,都是建基于民主体制,我们所处的是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国体——人民民主专政。但是理论的借鉴意义还是存在的。
[45]利玛窦1605 年在《圣经约录》中记录的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 , “形哀矜七端”:“一食饥者,二饮渴者,三衣裸者,四顾病及囹圄者,五舍旅者,六赎虏者,七葬死者”和“神哀矜七端”:“一启诲愚蒙,二以善劝人,三责有过失者,四慰忧者,五赦侮我者,六恕人之弱行,七为生死者祈天主。” 关于西方慈善思想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地方善举以及地方自治,日本学者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中有涉及。
[46]赵建敏神父有教会经历了恢复期和修和融入期两个阶段的说法,参见其论文“当代天主教的社会服务”,2006 年12 月1-3 日挪威奥斯陆“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本文参考赵建敏新浪博客,www.m.blog.sina.com.cn/s/blog_a0261a9010143z2.html#page=4.,2018-5-14登入。
[47] 参见马英林,“坚持中国化方向,开创中国天主教爱国爱教事业新局面”,2016年12月27日工作报告,《中国天主教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专辑》,一会一团编印,2016,第21页。
[48] 参见进德公益基金会官网,http://www.jinde.org/Home/Department/index.html。
[49] 具体论述可以参见朱晓红,“当代中国的天主教社会公益服务:资源,基础和发展空间”,《当代宗教研究》94(2014。1):1-6。
[50]具体资料转引自一会一团官网,“中国天主教”, “中国天主教公益慈善与社会服务工作会议在汕头顺利召开”, http://www.chinacatholic.cn/html/report/14051917-1.htm,2018-5-14登入。也许是统计标准和方法的不同造成数字的减少,或者与国家或其它社会部门在这些等方面投入增加相关,但国家对从事幼儿和青少年教育的门坎增高、对宗教团体从业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
[51] 参见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的原则和宗旨,http://hkjp.easyweb.hk。
[52] 参见彭小瑜,“天主教社会思想对社会正义的理解”,《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2017.4):108-114。
[53] “民主协商”不同于“协商民主”,后者指20世纪末期在西方多元化社会呈现的民主新形式,体现在党派之间、政府和公民代表之间等具有共同决策权的主体之间的协商。而“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四项之一,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共产党作为决策主体,向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社会各界代表就决策和执行过程进行协商。中共十八大报告又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将之看做和选举民主、自治民主平行的一种民主形态,但是核心仍然是政协制度。参见求是理论网,“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http://www.qstheory.cn/dd/dd2012/xsmz/,2018-5-15登入。
[54] 天主教是以宗教团体的代表参与各地政协,主教一般为省市政协委员,资深的本堂神父、修女或教会平信徒专职干部则为区县政协委员。政协是参政议政的制度平台,政协代表由团体提名、当地党委评定协商,政协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公布。政协委员产生整体上是邀请制,而不是选举制。
[55] 这是十八大以来的宗教工作理论新提法,参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宗教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18/c40531-29542397.html,2018-5-14日登入。
[56] 其实如果放弃或拒绝这种机会,可能还会有相应的惩戒性的后果。比如2012年7月7日上海教区马达钦主教在其晋牧礼上宣布退出爱国会,次日被隔离,数月后被撤职。(爱国会是一个由政府倡导成立的、和天主教会对应的社会团体,虽然它和政协不属于同一个层面,但是通过它作为宗教界别团体,亦可以参政议政)。退出宣告,被视为挑战政治底线,是政治上不可靠的表现。
[57] 贫困线按照2011年每年2300元的标准,贫困人口为1.28亿,2016年贫困线为3000元,贫困人口是4335万,2017年为3046万,减少了1289万。参加 “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 2018-2-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2/01/content_5262903.htm, 2018-5-14日登入。
[58] 可参见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1日文章“收入差距加大 致‘弱势心理’蔓延”,本文参见东方财富网,http://money.eastmoney.com/news/1583,20101111104411273.html,2018-5-14登入。
[59] 最早由清华大学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提出,见本文注五。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收入差距加大、社会竞争不公、权利寻租等造成的,但也有学者宣称这种弱势是机会、规则和程序等社会权利分配不公平造成的,见田文富,“‘非竞争型弱势化’之权利贫困问题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6(2011.11): 57-60。
[60] 参见桂华,“阶级、‘怨恨’与宗教意识”,《文化纵横》1(2013.2): 104-108. 虽然不同意作者采取的还原论的做法,只是从宗教的社会功能去分析当今中国贫弱群体的信仰状况,但是其中的现象和部分结论具有普遍性。
[61] Cf.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and Auckland: An Image Book Doubleday, 1994), No. 2445, p. 647.
[62] 本笃十六世,《以正义与和平教育青年》(2012年世界和平文告),4号。
(注:本文原载于《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二期,本平台蒙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