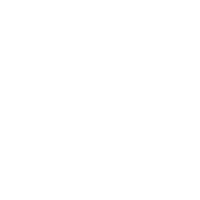编者按
自古以来,人类总为与神圣的相遇,设立专属的所在。诚然,上帝的存在并不受空间的限制;祂无处不在,随时可被遇见。然而,当人与上帝在某个特定之地相遇,那地方便超越了地理的概念,成为意义的所在:承载信仰、历史与人心的交汇点。基督徒称之为“教堂”,这是神与人相遇的“某处”,也是灵魂得以安歇、思想得以升腾的所在。
本系列将带领读者走进世界著名的教堂,领略建筑的艺术之美的同时,更去感受那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石墙之间,历史的长河里,人与神相遇的瞬间,如何化为永恒。即使人心败坏,世界支离破碎,美依然拥有拯救的力量。
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堂
人类走向二十世纪时,西方世界曾满怀信心地讲述着一个关于“进步”的故事。人们相信,新生的力量,诸如,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日益高涨的世俗主义、不断突破的科学,将像势不可挡的浪潮,席卷并取代旧的生活方式。这些运动坚定地立足于“今世”的道路,而非指向缥缈天堂的超验之途。在这股以理性与物质为核心的新思潮审视下,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基督教,自然成了被挑战甚至被否定的对象。
进步幻象与上帝的“退场”
当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时,他意图撼动的不仅是一位神祇的存在,更是整个西方文明赖以构建意义的世界图景。如果那位人格化的、与人立约的上帝不复存在,那么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核心、连接神圣与人性的一切理解,似乎都成了过时的叙事。二十世纪初的乐观主义者们,预言着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的黄金时代。然而,现实很快露出了冰冷的面目。两次世界大战的烽火、极权主义的幽灵、集中营的烟囱与古拉格的冰霜,接连击碎了“文明”必然线性向前的迷梦。
人们逐渐意识到,许多曾被自豪地归为“现代文明”基石的观念,比如,从国际法的准则到个人权利的尊严,从对弱者的怜悯到对正义的渴望,其精神经纬,竟深深编织于基督教的传统沃土之中。前几个教堂故事中或许探讨了基督教如何塑造了一个世界;而这里要追问的,是这个世界如何在新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下,才恍然察觉自身与这一传统的血脉关联,以及当人们雄心勃勃地试图将道德与公义等终极问题,完全收归人类理性与权力的掌控时,究竟引发了怎样的后果。
这个崭新又混乱的世界,向基督教抛出了一个尖锐到几乎致命的问题:一个以全然慈爱、绝对公义之神为核心的信仰,如何在一个处处可见不义、时常弥漫邪恶,且其信徒常成为加害者或旁观者的世界里,依然保持其可信性?当“什么是对的、善的、真的”变得愈发模糊,成为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彼此厮杀的信条竞相争夺的定义权时,二十世纪非但没有成为人类告别野蛮的黎明,反而成了各种“新神”在全球施加恐怖与死亡的世纪。“公义”这一概念,变得前所未有的飘摇与危险。
伯明翰的伤痕
要理解这种信仰与现实间的尖锐对立,以及在一个剧烈变动的世界里,“基督教的公义”究竟意味着何种沉重而具体的实践,或许没有比美国南部腹地更充满痛苦、矛盾与细微差别的舞台了。随着二十世纪推进,在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幻灭后,美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老欧洲更加坚定地自视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然而,这也意味着,在一个因种族、阶级而高度撕裂的社会里,对同一位上帝的信仰,竟能演绎出天壤之别的实践。当制度性的暴力在“吉姆·克劳法”的阴影下屡屡爆发时,“公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便以最残酷的方式砸在每个人面前。而吊诡的是,对这个问题的每一方回答,几乎都声称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塑造。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第十六街上的那座浸信会教堂(16th Street Baptist Church),正是这样一个凝聚了所有张力与痛苦的焦点。它的建筑朴素得近乎严肃,没有哥特式的尖顶,也没有彩绘的玻璃窗。这种刻意的朴素本身,就是一种神学宣告:浸信会传统坚信,信仰的核心在于内心的改变与圣经的话语,而非外表的辉煌。这座教堂的历史,就是一部黑人社群在奴役枷锁挣脱后,于新式压迫中寻求尊严与解放的缩微史。它始建于1873年,由新获自由的黑人信徒创立,并迅速成长为社区的心脏。它不仅提供属灵的慰藉,更在教堂地下开辟出房间与办公室,为在种族隔离下被系统性剥夺教育、法律平等权利的同胞提供切实帮助。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因其对公义坚韧不拔的承诺而闻名。
这份承诺,最终引向了荣耀,也招致了难以想象的惨痛。1963年9月15日,一个主日学的早晨,阳光与往昔并无不同。十四岁的辛西娅·韦斯利、卡罗尔·罗伯逊、艾迪·梅·柯林斯,以及十一岁的卡萝尔·丹妮丝·麦克奈尔,在教堂地下室的洗手间外,彼此帮忙整理衣裙和发饰。就在此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撕裂了周日的宁静。三K党成员预先安置的炸弹爆炸了。四名女孩的生命,在最天真无邪的时刻,被赤裸裸的仇恨瞬间吞噬。
教堂之所以成为目标,正因为它是民权运动在伯明翰的灯塔与堡垒。就在同年四月,马丁·路德·金博士正是从这里的台阶出发,带领游行队伍走向市政厅,抗议种族隔离的不公。他在随后被捕入狱期间写下的《伯明翰监狱来信》,雄辩地将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置于基督教“出埃及”和耶稣受难的宏大叙事之中。这使得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在捍卫旧秩序者眼中,成了必须摧毁的象征。
针对孩童的卑劣暴行,像一记重锤,敲醒了无数美国人的良知。爆炸的硝烟尚未散尽,悲痛与愤怒如潮水般涌动。此时,教堂的牧师约翰·克罗斯站了出来,他强压着自身的震惊与哀恸,通过一只临时找来的扩音器,以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开始诵读《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古老的诗篇,如同一道宁静的堤坝,试图拦住即将决堤的暴力。在随后的葬礼上,讲道人呼吁以“保持冷静、美善、仁慈、纯真”来纪念逝去的孩子。讽刺而深刻的是,那个主日学原定的课程主题,正是“饶恕之爱”。幸存下来的会众,决心行走在这条近乎不可能的人间道路上。
然而,废墟之上,信仰最深的拷问也升腾而起:如果上帝是公义的,祂当时在哪里?祂所应许的公义,又在哪里?世俗意义上的司法公义并未迅速降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在當地白人社区的“沉默之墙”前举步维艰。首名罪犯直到1977年才被定罪;最后一名则于2001年才被绳之以法,其间已逍遥三十余年。辛西娅的父亲克劳德·韦斯利,在得知首次起诉的消息时,只是平静地说,他希望“公义能够得到伸张”。这平静之下,是多少个日夜的煎熬与疑问。
这便引向了那个萦绕不散的核心问题:一个宣称上帝既全爱又全能的信仰,如何在一个公义迟来、恶行常胜的世界里,保持其可信性?公义为何如此缓慢?为何允许无辜者承受这样的苦难?许多人的心中,都不由自主地回响起旧约先知哈巴谷那撕心裂肺的呼喊:“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
当人自命为公义的仲裁者
上帝是公义的终极来源,却也带来一个难题:如果上帝的心意是唯一标准,而人又难以完全看清,那么谁有资格在世间“辨认”并“执行”公义?更进一步,如果有人坚信自己掌握了上帝的心意,他是否就能超越一切人间法律与道德?
历史用鲜血写过许多肯定的答案。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农民领袖托马斯·闵采尔坚信自己直接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他鼓动信徒“铲除不敬虔者”,要用暴力清洗世界,建立上帝的公义国度。在他眼中,教会的忍耐是懦弱,社会的改良是虚伪,唯有革命才符合神意。最终,他的军队被击溃,他自己也被斩首,头颅悬于城墙,成为狂热代价的冰冷警示。
时间跳到二十世纪末,这种“越权”在高度现代化的美国以更复杂、更可怕的方式重演。“大卫分支派”的领袖大卫·科雷什凭借对《圣经》预言的熟悉,建造了一个封闭的末世王国。他自称是《启示录》中“展开书卷的羔羊”,拥有解释和执行上帝审判的绝对权力。当执法部门介入时,科雷什视之为“邪恶势力”对“上帝选民”的围攻。1993年4月,一场大火与枪战带走了八十六条生命,包括许多儿童。讽刺的是,同样是那篇抚慰人心的《诗篇》第23篇,在科雷什口中却成了号召死战的檄文。
从闵采尔到科雷什,历史一再显示:一旦个人或团体自以为垄断了神圣公义的诠释权和执行权,就很容易走向排他、自义与暴力。他们试图在人间强行建立完美的“上帝之国”,结果往往造出更深的地狱。然而,这些只是信仰光谱上最刺眼的极端。在基督教历史的长河中,更常见的是另一种看似“软弱”却坚韧的形态:在忍耐中盼望,在行动中顺服。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会的普莱斯牧师曾给出不同的回答:“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会在他的时间里施行公义,而不是在我们的时间里。”对他而言,公义的延迟不表示上帝缺席;教会的使命是在等候神最终的公义审判之前,通过教育、服务、对话与非暴力抗争,在生活中活出爱与公正,同时把终极的审判谦卑交托给上帝。他常引用先知弥迦的话:“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里,公义不是由人发起并终结的战争,而是与上帝同行的生命旅程。
在破碎世界中的充满盼望
对于大多数身处主流传统的基督徒而言,基督教关于公义最深刻、最革命性的贡献,在于它将“爱”不可分离地编织进了公义的核心。当律法师问耶稣哪条诫命最大时,耶稣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从此,公义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律法条文,而是要以爱为出发点、以爱为衡量、以爱为成全。这一观念深刻塑造了西方文明,从十字架到人权运动,都渗透着这种爱与公义交融的精神。
然而,“神就是爱”的宣告,并没有消除世间的苦难与不义。这促使基督教神学必须直面“恶的难题”。早期教父爱任纽认为,人类被置于一个充满试炼的世界中,通过自由意志不断选择善、效法基督,灵魂得以锻炼成长,最终走向与上帝的合一。在这种理解中,苦难成了“灵魂塑造之谷”,公义在漫长的救赎历史中逐步实现。
奥古斯丁则提供了另一条思路。他认为,恶是“善的缺失”,源于人类以自由意志背离上帝。人无力靠自己纠正扭曲,唯有依赖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显明的恩典。公义首先是上帝的工作,然后才是人在恩典中的回应。这两种思想传统,影响了历史上基督徒面对不公时的不同姿态。罗马帝国晚期的波爱修斯身陷囹圄,在狱中写下《哲学的慰藉》,坚信至善的上帝终将伸张正义,最终坦然受刑,展现了在苦难中坚信善必胜的古典风范。
二十世纪的德国牧师朋霍费尔则走上了另一条路。他因反抗纳粹被捕,一生警惕“廉价的恩典”,主张真正的恩典是“昂贵的”,要求信徒为爱与公义付上代价。他拒绝逃离,选择与同胞共担苦难,最终在集中营殉道。他的生命成了“依靠恩典作出牺牲”的现代见证。圣经《启示录》为这一切挣扎描绘了终极盼望:“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公义完全实现、爱得最终胜利的景象,也是基督徒共同的盼望终点。
无论是认同“灵魂锻造”之路,还是“恩典依赖”之途;无论是积极投身变革,还是默默祷告行善,基督徒所仰望的都是同一个景象:基督终结一切不义与悲伤,让“以前的事”真正成为过去。
在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一个曾在种族隔离时期遭受爆炸袭击的历史遗址——普莱斯牧师将历史、神学与实践凝聚成一种具象的智慧:“我们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体。”这座教堂既是沉重记忆的承载地,也是鲜活敬拜的群体,更是指向未来宽恕与和解的记号。在黑人被剥夺许多基本权利的时代,这里曾是少数能自由祈求公义、倾诉痛苦的空间之一。普莱斯牧师说:“敬拜与公义紧密相连,一旦分离,二者都会破碎。”
二十世纪的教训表明,对公义的追求,应当是一种“活出来的祈祷”,不仅用口诉说,也用脚行走、用手劳作,甚至用生命献上。这需要坚韧,其力量不来自掌控世界,而恰恰源于那挑战世界逻辑的教导:“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那么,在终极公义降临之前,人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公义是否可能?普莱斯牧师的回答简单而深刻:“当然是可能的——耶稣已经显明这是可能的。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如今也拥有同样的能力,只要我们顺服上帝的道路。但问题在于:这很艰难。”正是在这种坦诚“艰难”却依然持守的盼望中,在这种让爱与公义永不分离的实践中,基督教走过了危机与重生的二十世纪,并继续面对未来的拷问。公义,始终是一场在历史中进行的、既神圣又属人的艰难求索。而信仰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赋予人在这条路上不至绝望的勇气,以及看见那超越现世之光的盼望。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