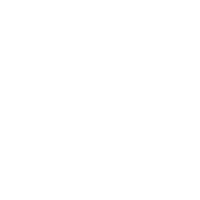摘要
贺麟对现代人的恋爱观曾经作了一个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基督教信仰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人的恋爱观。本文章讨论贺麟的观点、古希腊人和现代人的恋爱观以及基督教对爱情的净化和提升。
1)导言
现代的人很喜欢谈论爱情和恋爱,而学术界对这些感情和经验的反思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的好文章,比如Paolo Santangelo史罗华的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Tradition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Love《中国与欧洲‘爱情’概念化的宗教影响》和关启文的《性革命:文化、哲学和宗教角度的反思》。[1] 我认为,贺麟先生于1947年写的一篇“旧文章”还是很值得重新读的,因此从这个出发点来谈谈基督教与爱情的关系。
2)贺麟的观点
贺麟先生(1902-1992年)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哲学家之一,对德国哲学、欧洲文化和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有深入的以及“合情合理”的理解。他对近代华人的思想也有非常细致的观察并于1947年出版《50年来的中国哲学》和《文化与人生》两本书。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有一篇以“电影与文化”为题的文章。[2] 贺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话,比如:“外国影片十分之九以上都是涉及爱情的片子或穿插有爱情故事于其中的片子。……中国观众所最易了解,最易受影响的,即是电影中关于男女恋爱一方面。不过,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话,中国观众,特别青年观众所受的坏影响,亦以此方面为多,然而恋爱是西洋青年男女生活的核心。任何青年男女差不多都作过‘情人’,为什么中国青年男女看了西洋的爱情影片,就会有坏影响呢?橘逾淮而为枳[3]。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在西洋不见有什么流弊,为什么搬到中国来,就会令许多人堕落呢?”[4]
贺麟先生的主要关切是在“自由恋爱”中保持道德原则。他所说的“堕落”大概指不道德的性行为或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他认为,“当情人”是西方青年的自然经验,甚至说“恋爱是西洋青年男女生活的核心”是为了强调爱情的重要性。然而,根据贺麟的观察来看,西方青年在谈恋爱时似乎不会“堕落”,他们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某些基本的原则。贺麟的问题是:中国青年为什么一接触美国电影就不能“自拔”呢,为什么不能确保自由和对方的自由呢?
贺麟先生回答说:“这个原因很简单。自由恋爱的意义我们没有弄明白,男女恋爱的崇高理想,我们没有。男女恋爱的文化背景[原文:‘背境’]——社会的、文艺的、宗教道德的背景,我们没有培植好。只在电影中看见一些接吻、跳舞、装饰、游玩宴饮等等作爱的外表迹象,便去模仿,那怎么不发生流弊呢?即以男女恋爱一事而谕,在西洋至少有三个精神来源。第一为基督教精神,将基督教仰慕上帝,崇拜上帝的深情,移之于仰慕女性,崇拜女性,将女性神圣化。第二为中古骑士侠义之风。骑士尊重女子,敬爱女子,出死力以保护女子,拯救女子,纯出于侠义之气,决无猥亵淫邪的行为。第三为近代浪漫文艺。尊崇女性,以女性为永恒的美之象征,以情人为无限理想的寄托。认女性为艺术的保护者,为灵感的泉源,将女子神圣化,理想化,而加以爱慕歌颂。基督教精神、侠义精神、浪漫精神,三者缺一,决不足以了解西洋人男女恋爱的真意。这样讲来,看外国电影的人虽多,外国影片中,爱情片子虽多,但能真正了解爱情片中所潜伏着许多精神的和文化的背景的人,自然就会异常稀少了。”
这是贺麟先生的分析。他用几句话概括整个欧洲文化的爱情精神,真可说是深入浅出。他一开始阐述,恋爱的精神根源是三个因素,但后来又强调,这三个因素都来自基督教信仰。他说,近代的浪漫精神实际上是“西洋宗教传统中崇拜上帝之表现。将忠实的基督教徒崇拜、仰慕、歌颂上帝的情绪和态度,转而崇拜、仰慕、歌颂女性,便恰好不多不少足以代表西洋近代化的浪漫主义者对于女性的情绪和态度”。[5] 当然,贺麟所说的“骑士侠义精神”也是基督教中世纪的产物,与基督教信仰具有密切关系。[6] 所以,三个文化因素与基督教都是分不开的。因此,贺麟也许会说:“没有基督教精神就没有新的爱情观,就没有现代人的恋爱观!”最有意思的是贺麟对于第一个因素的说明:他认为,《圣经》中对上主的祈祷文表达一种内心的渴望——人心对神的渴慕。在祈祷中,人求上主的爱,就象男人求女人的爱。基督教精神将“爱神”与“爱人”联系起来了,所以被爱的对象(女人)就受了崇高的尊敬和爱慕。换言之,女性的尊严是神圣的,但其前提是,人们在上主那里首先体会到了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尊严”。
贺麟先生进一步说,“在过去,支配中国人生活最主要的两个权威为君与父。杨、墨无父无君,被孟子斥为禽兽。在家庭崇拜父亲,在朝廷崇拜君主,是中国人的纲常名教。但君父的观念,在西洋人生活中却没有取得主要中心的地位。反之支配他们生活的中心观念,一为上帝,一为爱人……他们有时为了崇拜上帝而牺牲爱人,如中世纪之节欲苦修的人,修道院中之僧侣及女修道士。他们有时又为爱人而牺牲了上帝,如近代有许多有革命性的无神论者和浪漫主义者。”[7]
当然,贺麟的分析也有所局限性,比如他似乎将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说西方人主要崇拜上帝和女人,而华人只认识“父”和“君”。不过,他的观察有很大的贡献。首先,他意识到,《圣经》的许多祈祷是对于一个“你”发出的心声,所以它们培养了一种“有感情”的文化,一种“追求对象”、“与对象要对话”的心灵。上主是人的“知己”和“良友”,他是一个有情有理的实在。第二,对于神的爱慕可以转向人:爱神和爱人有关系,神的尊严和人的尊严有关系![8]
3)爱情的“堕落”:从古希腊到弗洛依德
人在爱情上的“堕落”是古今中外的经验。从贺麟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人应该“渴望一个神圣的对象”、“牺牲自己为保护妇女”和“与理想化的妇女进行对话”。然而,人们多次仅仅追求自己的快乐,在爱情上进入一种道德的困惑,违反一些基本的原则。从某个角度来看,人的堕落是出于“榜样”的不足。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宗教信仰没有提供好的爱情观,人们也不知道应该遵守哪些原则和标准。
在古希腊社会中,人们崇拜很多男神和女神并制造了许多裸体的神像。在他们的神话中,最高的神——Zeus、Poseidon等——就追求人间的美女(比如Europa)。最高的神自己崇拜女性,这是什么意思?岂不是贺麟所说的“女子崇拜”?古希腊男女神明们之间的爱与恨对人间的爱情会有什么影响呢?古希腊人的Zeus拥抱了那么多女孩子,这是什么“骑士侠义”的精神?实际上,古希腊古罗马的多神论就表现出很多性崇拜因素和一种“无所不在的爱欲”。另一方面,Stoa(一译斯多亚)的理性精神和这种爱欲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Stoa的哲人所爱慕的对象是“命运”、“法律”、“宇宙之理”,但不幸的是,这些观念都是一些无情的铁律,是冷漠的,没有人格的(impersonal)。这样,古希腊人失去了真正的爱情,他们一方面崇拜肉体,但另一方面又冷漠地说肉体是灵魂的坟墓。
20世纪的“性革命”来自一种类似的现象:一方面,弗洛依德(Freud)告诉人们:性的欲望是无所不在的,而人心似乎只是性欲的傀儡。男女结合被视为人生的高峰,是幸福的极点,是神圣的。美丽的女子受崇拜如神。与此同时,男女关系在某些方面成为“无情的”、占领性的、非人格化的、随便的、肉体上的而非“灵魂的对话”。正如古希腊人将爱欲神化了,现代的人似乎要陷入于同样的困境和同样的“堕落”。
贺麟将“上主”和“女子”相提并论,说西方人对上主的崇拜转向妇女的“崇拜”,但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对象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人不是神;人不可以“崇拜”人,只可以“崇拜”神。如果宗教感情完全转向人间,就是彻底的“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必然会导致宗教、道德和爱情的堕落。在西方语境中,一个“崇拜女人”的人无非就是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的华人改革者多想将“祖先崇拜”转为“妇女崇拜”和“青年崇拜”。所以,他们喜欢古希腊神话并(和尼采一样)反对基督教。[9]
4)基督教对爱情的净化
基督宗教在爱情观方面具有精致的秩序。在基督宗教那里,上主是最高的价值;他的法律、他的圣言、他的智慧和正义都是人们爱慕和保护的对象。另外,《圣经》也要求人们关爱别人甚至同情动物。[10]基督教反对人的“无情”,因为上主本身是“有情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反对一种“色情泛滥”,因为上主对人的爱是神圣的、无私的、圣洁的。在基督教那里,人格深受“神格”的影响:“上梁正,下梁不歪”。[11]基督教解放人的宗教感情和对别人的爱心,同时也提出严格伦理要求来节制人的情感。——基督教对男女爱情的改造有几个方面:
第一,基督宗教的爱心要“宽”:首先,《圣经》要求人们爱慕上主“在万有之上”,要求人爱慕他的话、他的法律、他的正义和智慧。这样,人们应该珍惜精神价值。另外,《圣经》也指出,上主所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是美好的,而人们应该爱护这些。无论是音乐、葡萄酒或美食,都能带给人喜乐。这样,男女之情只是很多种“爱”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体验。《圣经》要求人们有一个宽大的心怀并关爱那些本来不吸引人的人。爱穷人或弱小者也就是基督教的博爱与“超自然的爱”,与古希腊人的“爱美丽、爱优秀”有所差别。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学说,爱有三种:欲望之爱、欣赏之爱与仁慈之爱(amor concupiscentiae, amor complacentiae, amor benevolentiae),而基督教特别培养第三种,即仁爱和同情(agape)。由此可见,基督教要“扩展”人心,要求人们关心很多“对象”:亲友、“远人”、穷人、病人、孩子、社会、法律……神。这种“博爱”也带给人们另一种自由:“守贞”(独身生活)的自由。换言之,人有不结婚的选择并仍然能够过一种充满爱和意义的生活。
这种“宽度”的根源是什么呢?本来是上主对以色列的爱。以色列在《圣经》中是上主的“爱人”,而上主在一切万民中特别爱护以色列人。但是《圣经》又肯定,上主也创造并养活其他的民族,他也爱所有的人。这种宽度也就是一神论的特点。多神论中的神不能那么普遍地爱惜所有的人,比如雅典娜就是雅典人的守护神,她具有地理限度。
第二,基督宗教的爱心要“真”,也就是说:人们应该真心爱慕对象,应该真诚地对待他并真正地认识他。《圣经》要求人们“全心全灵全力爱慕上主”(《申命记》Dtn 6:5)。人必须认识他所爱的对象和这个对象的特征。在宗教生活上也是一样。其它的古代民族也许在多神论的崇拜中“饥不择食”。人们也不太“认识”他们的神。但是,《圣经》说,信徒必须认识上主,认识上主的话、他的旨意、他的法律等,这样才能够“爱”上主。在人间的爱情上也必须澄清自己的感情,必须认识对象,不能欺骗自己或欺骗对方。人必须作出一个commitment(“投入”),必须作决定,必须全面地接受一个对象。《圣经》中的上主反对一切形式化的崇拜(见《以赛亚先知》Is 1:10-15),他看人的内心,所以人们在爱情上也应该是真诚的。
这种真情的精神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上主对以色列民族的真情。《圣经》中的上主是最诚肯的“情人”,[12] 他全面认识以色列并清楚地表达出他的感情。与此不同,古希腊的神明们一方面不想认识他们的对象,(甚至还上他们的当),而另一方面只追求一时的欢乐。Zeus那种“捻花夺笑” 和“一走了之”就是一个例子。在多神论中只能有一个“对象多,但没有一个爱人”的现象。看起来,Zeus和贾宝玉在情感上似乎是双胞胎!
第三,基督宗教的爱心要“深”,也就是说,爱情必须经得起考验。人们必须接受对方的缺点,必须宽恕他所犯的错误。因此,爱必须是一个对话,一个过程,一种深远的沟通。人间的爱容易流于“一厢情愿”或“单向的幻想”,而不是对话。然而,两个人的内心对话比外在的表现更重要。人们应该有丰富的灵性体验,才会感觉到“爱”与“被爱”的真义。
这种“爱的深度”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圣经》强调,人和上主——这个最可敬爱的对象——必须要有心灵上的沟通、对话、内心的表达。《圣经》的上主是一个说话的神,他愿意对话,他不仅仅要求人们的敬拜,但他也主动的“爱人”,甚至“爱这个充满黑暗的世界”[13]。上主的爱也经得起考验,因为他明明看到以色列的罪和“她”的“不忠”,但仍然照顾“她”。基督教的信徒可以体会到这种微妙的、精神上的“被爱”,他们的宗教信仰能“深化”人间的爱情。这与古希腊人很不一样,因为在多神论中,人们始终受某些神明的宠爱,同时也遭受另一些神明的嫉妒。Odysseus(尤利西斯)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
第四,基督宗教的爱心要“恒”:人们应该耐心地与一个对象走到底,永不放弃他,不离开他。这是人们的渴望,也是良好家庭环境的前提。然而,人间的爱情多次是断断续续的,谁能作出这样的承诺:“我会永远爱你”呢?
在基督教那里,神对人们的爱是“永恒的”(见《耶利米》Jer 31:3“我以永恒的爱爱了你”)。上主是“忠”于自己的诺言,他不放弃人们。耐人寻味的是,《圣经》说,人们虽然破坏上主的“盟约”,但上主仍然忠于他的“盟约”,他不收回他的诺言。上主是最忠诚的“爱人”,而他的榜样也应该影响基督教徒的生活。所以,人间的爱情也应该有“恒心”。人心渴望的还是“永远的爱与被爱”,而不是宙斯式的“一走了之”。
第五,基督宗教的爱心要“圣”:人间的自然爱情也许只是单纯的、粗糙的、一方面的,但《圣经》中的爱情都与神爱有关系。换言之,在《圣经》中,人间的爱比喻着一种更深远的奥秘:母爱比喻上主对人的照顾,父爱比喻上主对罪人的宽恕,男女之爱比喻灵魂与上主的密切关系。“比喻”的意义是,人生活在一个更大的、更深的奥秘当中:在神圣的爱当中。比如,《圣经·雅歌》就是一个例子:男女之爱暗示人神的密切关系。[14] 因此,男女之爱不仅仅是“肉体的事”,不仅仅是激素、冲动或单纯的“性”(sex),而总是整个人的爱,是一个奇迹,是一个奥秘,它始终有一层更宽、更真、更深、更恒、更圣的意义。为《圣经》中的人来说,人生活在上主的“圣爱”之中,而这个体验也会影响人间的爱情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精神基础,不会有现代人的恋爱观和爱情观。至少可以说,古希腊人的精神基础是不足够的。贺麟先生,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1] 见《基督教文化学刊》第4期(2000年),41-71页和185-226页。
[2] 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出版社,重庆,1947年,250-253页。
[3] 此成语来自《周礼·考工记》,“橘化为枳”指“因环境的变化而自己变化”。
[4] 同前引书,贺麟,250页。
[5] 同上,251页。
[6] 关于中世纪的爱情文化和骑士的风格应该作一个专门的研究。我们这里只简单地可以说,骑士的对女子的爱慕是贵族文化的表现;女子高高在上,她评价骑士的表演、他的行为和他写的情书;这种爱情文化很强调文化(爱情诗、爱情歌、骑士的文明举止、贵族的风格),可以说是另一种“以文会友”(见《论语》中的名言)。这种男人的求爱和对妇女的“服务”(Minnedienst, Frauendienst, 比如见Ulrich von Liechtenstein 于1255年写的长篇小说Frauendienst,参见Reclams Romanlexikon, Bd 1, 107-109)有另一个特点:它不怕男女之间的距离。英雄多次必须走很远才能回到他的情人来,而贵族的风格要保持爱人之间的强力和渴望,不让他们简单地结合。他们只能通过很多考验和牺牲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结合。
[7] 同上,251页。
[8]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因素确实是基督宗教的重大突破:第一,神是一个“你”,是对话中的“你”,是祈祷的聆听者,是心灵的“良友”和“嘉宾”。(与此不同,古代人的宗教经常缺乏这个神圣的“你”,缺乏一个“人格神”(personal God)或内心的祈祷文。)第二,对人的爱应该是神圣的,因为人是“上主的肖像”,他有崇高的尊严。(与此不同,古代人的宗教崇拜多次会忘记人的尊严,如古罗马帝国的国家宗教。)
[9] 见周作人《祖先崇拜》(1919年),载《理性与人道·周作人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4-5页“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亦见林语堂对于古希腊神话的爱好,见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0] 参见《圣经·出埃及记》Ex 23:4-5:《圣经》要求人们同情“仇人的驴子”。
[11] 参见张东荪的观点: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74页。
[12] 参见吴经熊《爱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ove),香港1940年。
[13] 参见《约翰福音》Jn 3:14。在《约翰福音》中,“世界”是黑暗的、充满罪恶的,但上主仍然“爱”它。
[14] 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受了当时西方学者的影响而否认《雅歌》的宗教含义,见其《〈旧约〉与恋爱诗》(1921年),亦见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同上,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