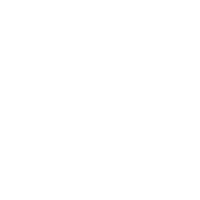公元六世纪末,罗马在受到洪灾肆虐和战争蹂躏后,又遭遇了黑死病“查士丁尼大瘟疫”的袭击。“查士丁尼大瘟疫”先后爆发五次,这是最后一次。黑死病夺去许多人的生命,马车上装满了尸体,罗马城沦为废墟;教宗帕拉纠二世也于公元589年死于瘟疫。
于是一个名叫格列高利、50岁、秃顶、体弱、当过罗马市长、后又长期潜心研究神学的隐修士,被推举为新一任教宗。但他拒绝就任,逃出罗马,遁入山林。直到被搜索出来并带回罗马后,他才于公元590年9月3日成为“圣彼得的继承人”。
新教宗告诉大家,瘟疫是上帝刑罚人类罪恶的结果,号召大家举行大规模的忏悔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位于台伯河畔罗马皇帝哈德良(公元76-138年)陵墓前时,教宗本人看见了异象:大天使米迦勒拔剑在空中挥舞,之后把剑放回鞘中。不久,黑死病流行就结束了。
为了感谢天使的庇佑,格列高利让人在城堡上立了一座天使手握长剑的青铜雕像,并改名为“圣天使堡”。连同圣天使堡下方那座横跨台伯河的桥,也被命名为圣天使桥,桥上立有十二尊天使像,手中各拿着一样耶稣受难时的刑具或相关物品。十二寓意耶稣十二门徒。
格列高利之所以坚信瘟疫源于上帝的愤怒,是因为在圣经的记载中,所有的瘟疫,都是上帝降罚的产物:
当以色列百姓因为可拉一党被剿灭而迁怒于摩西、亚伦,并试图攻击他们时,神用瘟疫杀了他们一万四千七百人;当驻在什亭的以色列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并拜假神巴力时,神再次用瘟疫杀了他们二万四千人;当大卫因受撒旦激动,在四境安靖时数点民众而惹动神的怒气时,神再次用瘟疫惩罚以色列百姓(神让大卫在三样惩罚中选择一样)。当瘟疫夺去七万名以色列百姓生命、天使拔刀指向耶路撒冷时,神瞬间心生怜悯,吩咐天使说:“够了!住了吧!”
转眼间,人类迎来了2020年。
这一年,离格列高利看见异象,过去了1430年。
这一年,来势凶猛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把安逸已久、拥有高度发达的医疗水平的人类打了个措手不及。瘟情所到之处,城市静默、小区封闭、家家隔离、人人自危;医院里人满为患,ICU超负荷运转,不断有重症患者死去。一具具尸体被源源不断地拉到殡仪馆,排成长队等待火化。其情其状,宛如末日!
2022年3月,《柳叶刀》发布最新研究,指出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或超过1800万,远远高于WHO统计的数字;至少有500万儿童,因新冠疫情失去父母一方或抚养人;而《金融时报》则声称新冠疫情“比想象的严重,是自西班牙流感以来最大的死亡人数冲击”,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瘟疫流行。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和1430年前的黑死病有何不同?
首先,“黑死病”这个名字很简单、很直观、很具象,而“COVID-19新冠肺炎”则要复杂得多,不但读起来拗口,记起来也不容易。
其次,黑死病袭击罗马时,人类还没有“细菌”这个概念,也不知道“鼠疫杆菌”是啥玩意儿,更不用说观察到它们了;而今天我们借助电子显微镜和射透显微镜,就能轻易观察到新冠病毒的“尊容”,测量到它的直径在60-140nm之间,并及时跟踪监测到变异的毒株。
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两个时代的不同。
出现黑死病的那个时代,虽然也犯罪(自始祖堕落后,人类就没有不犯罪的时代),但却是一个相信圣经所记载的全备真理、相信“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一1:9)的时代。教宗格列高利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举行了大规模的忏悔游行,向神谦卑悔罪,并蒙神怜悯。
而现今呢?
今天,是一个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
很多时候,人们把科学与上帝对立起来,认为科学与上帝誓不两立。常听到有人真诚而又充满疑惑地嘟囔道:“美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上帝?”他们不明白科学与上帝的关系,不晓得科学是人类研究、发现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和生命中所蕴含的内在规律并使其造福人类的一个系统工程;不明白科学是人类认识“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的造物主的一个途径,更不理解科学是上帝馈赠给人类的礼物,是上帝护理人类的一个手段: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正是用上帝赐予的医学知识和设备,来防疫、治病的。
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
但正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样,一个时代要“活着”,并非靠科学,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只是今天,还有多少人相信“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随着启蒙运动、进化论、××主义、圣经批判学、自由主义神学的兴起,以及人本主义、经验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的滥觞,作为“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载体圣经,不断受到怀疑、否定、攻击;人类因否认上帝而为所欲为,罪恶充满世界。于是他们又转而把这一切归咎于上帝,高喊“上帝已死”。
他们罢黜了真正的王上帝,立自己作超人、作新王。
人类作王,世界更美好吗?
喊出“上帝已死”没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在当时最具科技含量(人类在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一是教唆科学与上帝对立,二是使用科学来杀人)的世界性大战,导致3000万名士兵伤亡,使649.3万名平民丧命,而死于战争导致的饥荒等灾害的人数则多达1000万人。
而最最耐人寻味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士兵的背包里,装有这样的两本必备的小册子:一本是《圣约翰福音》,另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者说的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后者则藉查拉图斯特拉这位下山的隐士之口,宣告“上帝已死”。那些即将抛尸异国他乡的士兵,蜷缩在战壕里读书中尼采的诗句:“我教你们做超人。人是应该被超越的。”
1889年1月3日,尼采在都灵街头突然精神崩溃,抱住一匹马大哭不止:“我的受苦受难的兄弟呀!”之后被送进疯人院治疗。
尼采发疯三个月后,也即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诞生了。
阿道夫·希特勒继承了尼采的全部疯狂。由于德国法西斯和纳粹党一直以尼采作为其精神领袖,二战期间纳粹甚至整个轴心国都把尼采视作圣人,所以许多人都将尼采等同于纳粹,等同于法西斯。
阿道夫·希特勒诞生一年零四个月又五天后,即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了。
尼采死后,自由主义神学继续泛滥。
尼采死后98年,或者说在自由主义神学诞生一个世纪后,1998年美国社会学家哈登,曾用问卷的方式,请10000名美国新教神职人员回答4个问题。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是“你相信圣经在信仰、历史和社会事务上是神所启示、绝对正确的话语吗”?结果87%的循道宗人士、95%的圣公会人士、82%的长老会人士、67%的浸信会人士、77%的路德宗人士,选择了“否”!
窥一斑而见全豹,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今天这个时代的属灵光景了。
今天,外邦人高举科学与理性的大旗,否认上帝、否认上帝的存在、否认上帝的创造,认为圣经是杜撰出来的“神话”;而可悲的是,许多神的百姓甚至神的仆人,也是按着自己的认知、喜好、个人的善恶标准,有选择地相信圣经。私欲让我们变得无所顾忌,于是我们起来修正上帝的话语。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罪像今天这样丰富而又美好,它们色、香、味俱全,让人难以抵御。罪性未泯的人只要一摸、一看、一嗅,就会神魂颠倒、乖乖就范。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罗马爆发黑死病的时代,是一个犯罪但相信上帝、相信圣经的时代;而今天是一个犯罪又不相信上帝、否认圣经是全备真理的时代。
所以当2020年COVID-19新冠肺炎瘟情猝然而至时,我们除了加大口罩等防疫物资的产能、用“科学+诬陷”的方式进行所谓的“溯源”、匆促上马研发疫苗外,我们对疫情与罪的关系,闭口不谈。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北京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