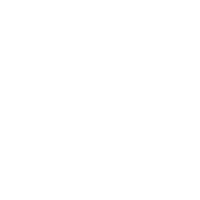2025年豆瓣读书小说类第一名的小说是《燕子呢喃,白鹤鸣叫》,这是一本小说集。这个诗意的书名,初看让人误以为是一部重意象、好修辞的精致之作。翻开后才发现,阮夕清的笔触竟如此朴实。他写的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无锡工人阶层的故事,是工厂转型时期那些模糊的面孔,是巷子口租书摊的昏黄灯光,是推着旧自行车收废品的人。这些场景太熟悉了,熟悉到几乎被记忆遗忘。作者刮开时间积下的灰垢,让那些曾经鲜活的瞬间重新呼吸。
小说集收录六篇短篇小说和一篇非虚构自传。阮夕清本人就是无锡人,1976年生,1999年发表小说,2009年停笔,十一年后重新拾笔,竟接连获奖。他的故事里有一股下沉的力量,沉入生活的底层,沉入那些被宏大叙事遗忘的角落。而全书同名的这篇《燕子呢喃,白鹤鸣叫》,让人脊背发凉。表面上是一个杀人犯的故事,内里却是一曲关于恐惧、孤独与濒临绝境时如何呼救的哀歌。
人发出的声音不再是语言
小说主人公是个普通的销售员,在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的浪潮里载浮载沉。他的犯罪并非预谋,更像是在生活的逼仄中一次失足的滑落。阮夕清没有渲染血腥,也没有刻意营造悬疑,他用近乎淡漠的笔调叙述着罪行的实施,以及之后那些看似正常的日子。凶手照常上班,应付客户,回家吃饭,只是在深夜会被细微的声响惊醒。
令人心惊的不是行凶的过程,而是被捕前那段时光里,凶手内心逐渐崩解的声音。他还能思考,还能感受,但某种东西已经死了。他活在人群里,却像隔着玻璃观察一切。恐惧不再是剧烈的阵痛,而是一种弥漫的、低浓度的毒,渗透进每个日常动作。在这种状态下,人发出的声音不再是语言,而接近一种生物性的哀鸣。小说里没有直接引用圣经,但阮夕清为这篇小说,也为整部小说集所选取的名字,却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状态:“燕子呢喃,白鹤鸣叫”。
这句话出自《以赛亚书》第38章。犹大国王希西家病重将死时,向神呼喊:“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望,眼睛困乏;耶和华啊,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燕子“呢喃”或“啾啾”,是短促、细碎、不安的低语;白鹤“鸣叫”或“嘎嘎”,是悠长、空旷、孤独的呼号;鸽子“哀鸣”或“呻吟”,是无助、哀伤。这三种鸟的声音,共同勾勒出一个濒死之人的心灵图景:他还有意识,还能感受,但属于人的、完整的语言系统已经崩塌。他无法再组织起宏大的论述或虔诚的告白,只能发出这些零碎的、本能的、动物般的声音。那是一种被剥去一切社会身份(即便是国王)后,生命最原始的颤动。
小说里的凶手,在罪行暴露的前夜,就处在这样的“希西家时刻”。他不再是销售员,不再是儿子或邻居,甚至不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被罪与惧压垮的生命体,蜷缩在黑暗里,从喉咙深处挤出无人能懂,或许也不期待被任何人懂的哀鸣。那呢喃与鸣叫,是他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脆弱的连接。
希西家的病榻
理解这篇小说,或许有必要回到希西家王的故事本身。希西家是犹太历史上一位难得的贤王,他推行宗教改革,废去邱坛,带领子民归向神。然而,在他生命鼎盛之年,却突然患上绝症。先知以赛亚奉命告诉他:“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这个宣告彻底击垮了希西家。他转脸朝墙,向神痛哭祷告。他陈明自己的虔诚与功绩,言语中不乏委屈与不甘,仿佛在问:“神啊,为何是我?为何在此刻?”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反应:在突如其来的苦难与不公面前,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质问,是依据自己过往的“表现”要求一个解释。
神奇迹般地医治了希西家,增添他十五年的寿数。而希西家在病榻上写下的诗篇(即以赛亚书38:9-20),却非即刻的欢庆,而是事后的沉思。他回顾自己从苦毒质问到谦卑顺服的过程,最终领悟到:“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苦难剥夺了他的健康、王的尊严乃至流畅的语言(只能如鸟哀鸣),却也将他逼到一个绝境:在那里,一切自义、骄傲和赖以生存的“身份”都失效了。他只剩下赤裸的生命本身,和向着至高者发出呼救的本能。
这破碎的、不成调的呼救,被神垂听。希西家在诗篇结尾说:“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请注意这个顺序:先是“呢喃”“鸣叫”“哀鸣”,然后才可能有殿中“丝弦的乐器”奏响的诗歌。没有前者那种在绝望中掏空自我的真实,后者就可能流于形式与空洞的赞美。
阮夕清小说里的凶手,没有希西家那样的信仰归宿。他的“哀鸣”可能没有指向神,甚至没有明确的指向。它只是一种存在状态的音效,是灵魂在重压下变形时发出的吱嘎声。对这种声音的仔细聆听与刻画,让这篇小说获得了惊人的深度。它让我们看到,罪与罚的故事外壳之下,是一个关于“人如何在精神濒死状态中存活”的普遍命题。我们或许不曾杀人,但我们都可能在生活的某个时刻,感到自己被某种东西“杀死”了一部分,从而陷入那种失语、只能“呢喃”的状态。
“没有生活的生活”
回到小说集整体,阮夕清写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希西家时刻”。不只是罪人,也是普通人,在时代转型、生活无以为继的关口,发出的那些微弱声响。《运河铁人》里,那个从河床捞起、代表一个时代工业梦想的机器人残骸,是一种沉默的“鸣叫”。《窗外灯》里,父亲那个最终走向毁灭的同事,他的一生就是一声拉长的叹息。《八音枪》里,叙述者在冬夜漫想那些“除我之外不会有任何人在乎”的失去,这些失去本身,就是细碎的“呢喃”。
阮夕清在自述文章《试验针、鬼故事和燕子呢喃》里,回忆了童年两件小事:一是因怕打“试验针”逃学,却发现学校一切如常,自己“在不在都无所谓”,初次感到被世界遗弃的恐慌;二是听一个智力衰退者讲鬼故事,故事里的少年们没有来历、没有家庭,如同凭空存在,这带给他对“存在”本身的困惑。他说:“写作让我发现了一群人的微不足道和略等于无。”
这是阮夕清写作的起点与核心,关注那些“没有生活的生活”,那些“略等于无”的存在。他用小说为这些微不足道的时刻建档,让那些即将消散在时光里的“呢喃”与“鸣叫”,获得一种文学的形态,从而被听见、被记住。
圣经里,希西家的哀鸣最终引向了救赎与赞美。而在阮夕清的小说世界里,人物的“哀鸣”往往没有这样明确的彼岸。但文学不是说教,它记录下它们,本身已是一种对抗遗忘的表达。它告诉我们,那些看似“没有生活的生活”,那些只能发出“呢喃”与“鸣叫”的生命,同样值得被凝视,被讲述。也让读者看到普标的人性状况,而生出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救赎的渴望。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