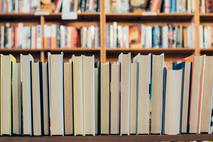问候亲爱的读者平安!我们继续分享这个题目。
中国现代文学的耶稣受难书写主要体现在客西马尼园中其受难心理的披露及十字架上受死的场景。在思想上主要呈现出神性被遮蔽、人性被彰显的世俗性特征,在美学上则具有独特的悲剧性质素。中国现代作家对耶稣受难题材的钟爱与时代语境及个人体验的契合,以及悲剧性题材的独特魅力相关。对耶稣受难书写进行论析可以清晰地勾勒本土化的耶稣形象,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下的基督论进行生动而形象的回答。(孟令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耶稣受难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和卓有成就的作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先生虽然站在怀疑批判的立场上对待基督教,但他并未将基督教文化完全否定和抛弃,他曾多次推崇基督的钉十字架的精神。1924年他在《孤鸿》一文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他由看了《往何处去》的电影中的情节而生感慨。“感动我的不是奈罗的骄奢,不是罗马城的焚烧,不是培茁龙纽斯的享乐的死,是使徒彼得逃出罗马城,在路上遇着耶稣幻影的时候,那幻影对他说的一句话。他在路上遇见了耶稣的影子向他走来,他跪在地下问道:主哟!你要往何处去?耶稣答应他说:你既要背弃罗马的兄弟们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郭沫若说:“这句话真是把我灵魂的最深处都摇动了呀!……我那时恨不得回到你住的那Golgotha山,我还要陪你再钉一次十字架。”由此看来基督的钉十字架的精神感染了郭沫若。
三、中国现代作家受基督教影响
中国现代作家们是生长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必然在他们的心中烙上深深的印痕,儒家文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心理基础。这样,牺牲自我、拯救民众的基督也就很容易成为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们大多把基督作为人来看待,而不把他当作神来膜拜。“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中溢出基督的救世精神。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将耶稣受难的时间、地点和背景等信息全部隐去,从而使耶稣十字架受难这一场景带有很强的隐喻性。这里,围观耶稣受难的看客可以毫无障碍地被读者视为中国看客的现象。此外,作者故意抽去了福音书对耶稣受难表示同情之观者的描写。作品将“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诅咒的”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将耶稣置于绝对的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明确地揭示耶稣之死不仅仅缘于十字架之刑,亦在于围观群众的冷漠“看杀”。鲁迅通过对耶稣十字架之死的创造性改动,再一次指出了“看客”的麻木、愚昧、残忍与嗜血等特性,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而被看客“看杀”的耶稣也是失败的启蒙者、先觉者的隐喻。(《鲁迅全集》,第2卷)
周作人则说:“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是崇拜基督的一个人。”周作人在性心理学的影响中突出基督的人道色彩。著名女作家冰心“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中国五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童年就成为基督徒的庐隐女士则说:“当然以耶稣伟大的人格,博爱的精神,很够得上人们崇拜,我就以他为人生的模范,并不算坏。”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忽略基督的复活、圣灵、圣事等,而注重其中蕴含的博爱思想、人道精神、救赎色彩、人格意味,以此来否定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宿命思想、奴性性格等,这对于当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现代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与爱情有独钟,因此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纷纷在创作中营构充满着博爱色彩的温馨世界。周作人录写了倍受屈辱的妇女、儿童的悲哀生活,呼唤着尊重人性、平等自由的人道理想;冰心展示了对不幸者的同情、怜悯与温爱,建构着没有贫富智愚差别的爱的大同世界;许地山描绘着受尽磨难的坎坷人生,突出了主人公对人生的不倦追求、对世界执著的爱;庐隐叙写着寻觅人生真谛之途中的人们的奋斗与挣扎,凸现出对悲惨世界中人们的关爱与同情。
由于受到基督牺牲自我、救赎众人伟大精神的影响,在不少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具有牺牲精神的救世者形象:鲁迅的《复仇(其二)》生动地再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的悲壮情景和复杂内心;许地山的《玉官》描绘了面对欲施暴的兵士挺身而出、宣扬基督爱的教义的玉官的救世精神;庐隐的《余泪》叙写了只身上前线劝说上帝的儿女们不要互相残杀的白教师的献身勇气;巴金的《田惠世》塑造了为了抗日而不屈奋斗、不惜牺牲的基督徒田惠世的生动形象。在描绘、刻划这些具有牺牲精神的救世者形象时,作家们常常融入了对基督人格的崇拜之情。
中国现代作家中,有一些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的自身就是基督徒,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也常常把作品中的人物送进教堂的大门、拜倒在十字架下。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并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的苏雪林所写的《棘心》,细致地叙写了留学生杜醒秋信耶稣的曲折历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充满争议的作家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生动地描写了一对处于爱情波折中的青年男女受洗入教的过程;庐隐《女人的心》,把在婚姻悲剧中的主人公贺士送入了上帝的抚慰中;曹禺的《雷雨》,将经受了家庭悲剧的主角周朴园送进了天主教堂……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人物信耶稣,大多是在处于难以摆脱心灵的苦痛与磨难时,为求得情感的慰藉和心理的平静。
对于这方面,可参阅我在《福音时报》发表的系列文章《基督教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一、二、三)》。
鲁迅对基督教文化采取了客观辩证的态度,在对基督教历史的考察中,他指出中世纪基督教对科学精神、思想自由的压抑,也肯定希伯来文化的璀灿庄严及深远影响。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之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鲁迅道出宗教统治下思想、言论自由深受压制的状况。他对路德的宗教改革甚为推崇:“转轮既始,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益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
我们应该看到:自利玛窦以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求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乃以翻译的形式来进行。一方面,传教士与中国学者结合而将基督教圣经,以及大量教义、教理、释经、神学领域的著作译成中文,以求得中国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和与其相关联的文化体系对话、契合。此后,中国学者更是独立承担了这种翻译任务。如中文圣经的翻译,当今“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和“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等翻译。这种“求同”是在汉语语境中进行的,其长期积淀终于在当代中国触发了一种“汉语基督教神学”的建构和发展。这种神学构思以大量的翻译为基础,并在这种翻译过程中形成其信仰精神相契、语言表述独特的全新神学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传教士亦在中国学者的讲解帮助下将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译成外文而流传西方,在西方基督教会内外引发关注中国语言文化及其思想精神的“中国热”,从而促成了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的诞生及发展。这就是一方面基督教影响着中国的现代文学,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又影响着基督教乃至西方文学。这是一种双向的融合。海外汉学的历史,其起源和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乃为来华传教士之功,而其内容亦多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认同相关。这可谓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求同的外在发展。由此观之,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只要持之以恒、坚持下来,也会产生同样的功效,对中国当代或未来语言、词汇及精神表达带来新的内容、十分谨慎,而对海外华人的新译和大陆学界个人的重译亦持的形象。自圣经汉译的和合本问世以来,中国大陆基督教界对其新的汉译十分谨慎。如果我们透彻理解翻译的本质即解释,那么对于这些解释学意义的大胆探索则理应开放和支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树人(鲁迅)、周作人两位兄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在“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创作、周作人的理论倡导,成为当时文坛的两杆旗帜,影响与推动着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我们论及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时,也必然不能忽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对周作人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1921年周作人在给孙伏园的信中谈及他当时的思想说:“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同生活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基督教的思想构成了周作人复杂思想的一部分,对他当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主张、对他的散文创作等都有着一定的影响。1925年,周作人说了一句名言:“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是崇拜基督的一个人:时常现在我的心目前面令我最为感动的,是耶稣在殿里‘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划字’的情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我们读到这里,真感到一种伟大和神圣,于是也就觉得那些一脸凶相的圣徒们并不能算是伟大和神圣。”周作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十分崇拜基督,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影响最为深刻的是蕴涵在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简要归纳,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和文体方面,丰富了文学语汇:圣经的翻译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许多新词汇,如“洗礼”“天使”“乐园”“天国”“伊甸园”等,这些词汇在文学作品中大量涌现,丰富了作家的语言表达。
影响了叙事方式:圣经的叙事结构被一些作家借鉴,如鲁迅的《药》和《复仇(二)》、茅盾的《耶稣之死》等作品,都受到了圣经叙事方式的启发。
催生了新的文体:模仿圣经文体的“祈祷体”“赞美体”“书信体”等文体在中国文学中出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创新提供了借鉴。
主题和思想方面,提供了创作素材:圣经中的故事、象征和主题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一些作家在作品中探讨了基督教的精神,如爱、牺牲、救赎、造物主等主题。例如,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中客观地描写了基督徒的生活,展现了中国基督徒的多种面貌。
影响了作家的价值观:基督教文化中的博爱思想、人道精神、救赎色彩、人格意味等,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价值观产生了影响,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营构充满博爱色彩的温馨世界,否定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宿命思想、奴隶性格。如冰心展示了对不幸者的同情、怜悯与温爱,建构着没有贫富智愚差别的爱的大同世界;许地山描绘着受尽磨难的坎坷人生,突出了主人公对人生的不倦追求、对世界执著的爱。
文在化整合与现代性体验方面,打破了文学的封闭性:基督教文化的进入打破了中国文学的封闭性,促使中国文学对世俗与终极、批判与超越、自我与世界、身体与精神等问题有了复杂的关注和回应,创造了中国文学新型的传统意义和表达方式。
促进了文学的现代转型:基督教文化催生下的中国小说新情节模式,将圣经典故作为小说的文心,用其叙事框架作为小说的叙事模型,促进了中国小说的转型和发展。例如,由年号纪年到公元纪年的转变、基督教节日如圣诞节等进入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系统等,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时间中染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具有了迥异于传统的叙事风格。
在文学研究范式方面,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式从“反对论”“契合论”“矛盾论”发展到“整合论”,解构了传统的纯文学本体研究范式,激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相对停滞的局面,取得了一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参阅书目:
1.洪秀全:《原理醒世训》,见《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16页。
2.杨克已编:《民国康长素先生有为梁任公先生启超师生合谱》,商务印书馆1982年10月版,第268页。
3.《孙中山全书》第388页、第491页。
4.王治心:《孙文主义于耶稣主义》,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30年7月版,第5页。
5.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
6.周作人:《山中杂信》。
7.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8.周作人:《抱犊谷通信》。
9.冰心:《我入了贝满女中》。
10.庐隐:《其他·我的宗教》。
11.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之传播及其贡献》,见《道与言》,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2月版,第112页。
12.萧乾:《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13.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第100-101页。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