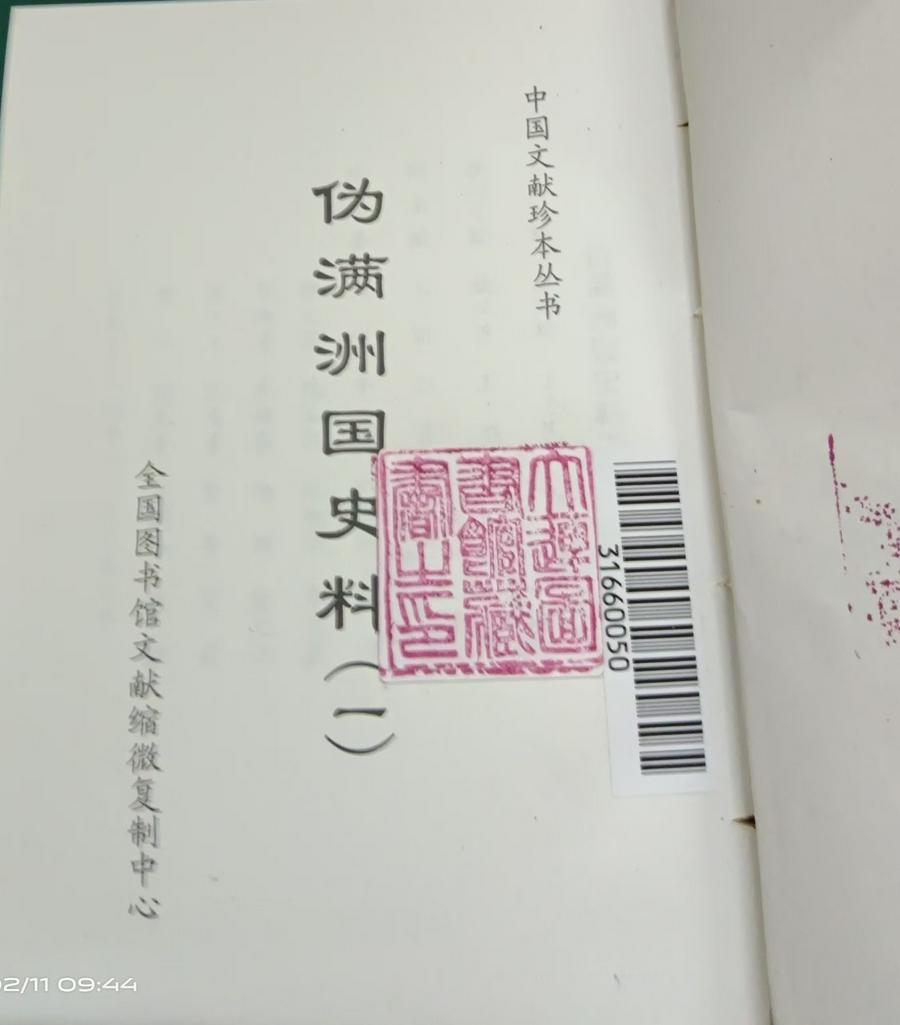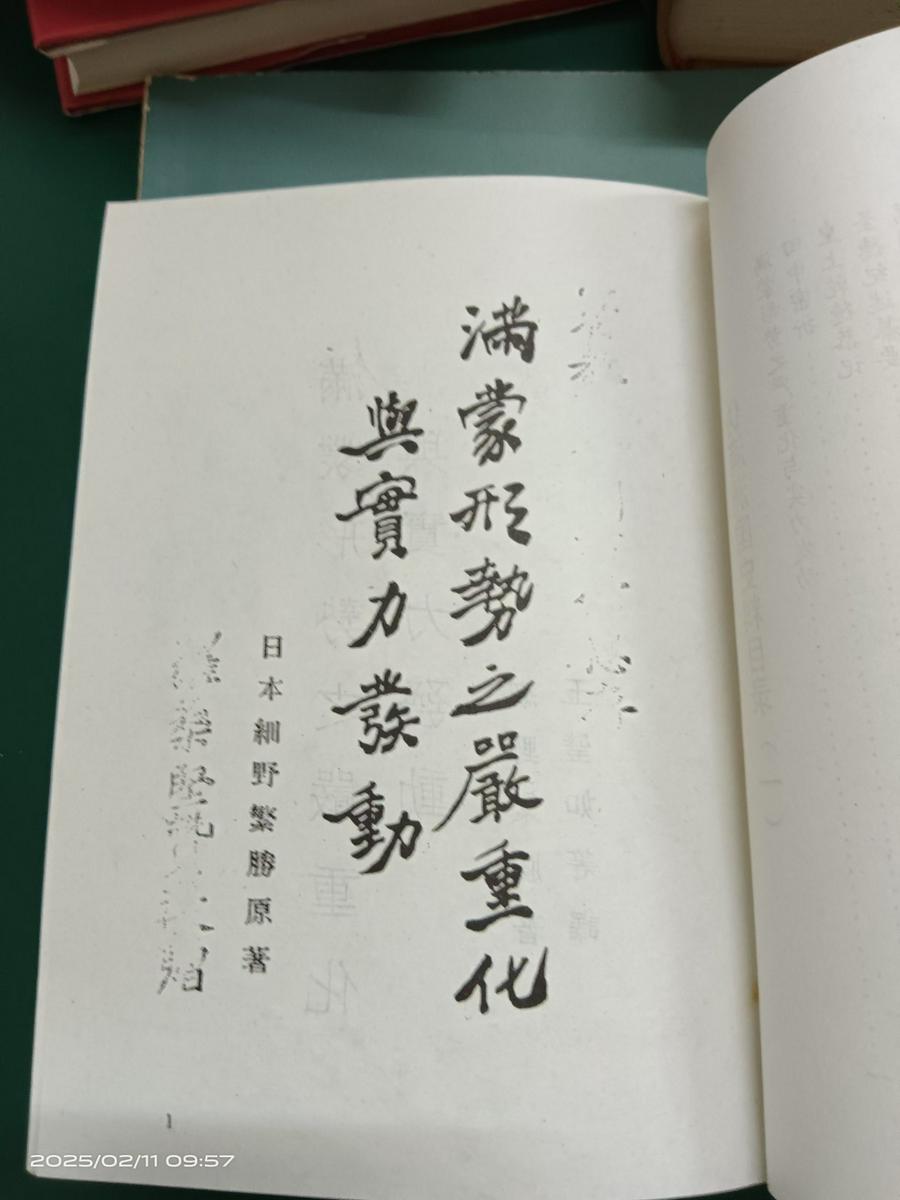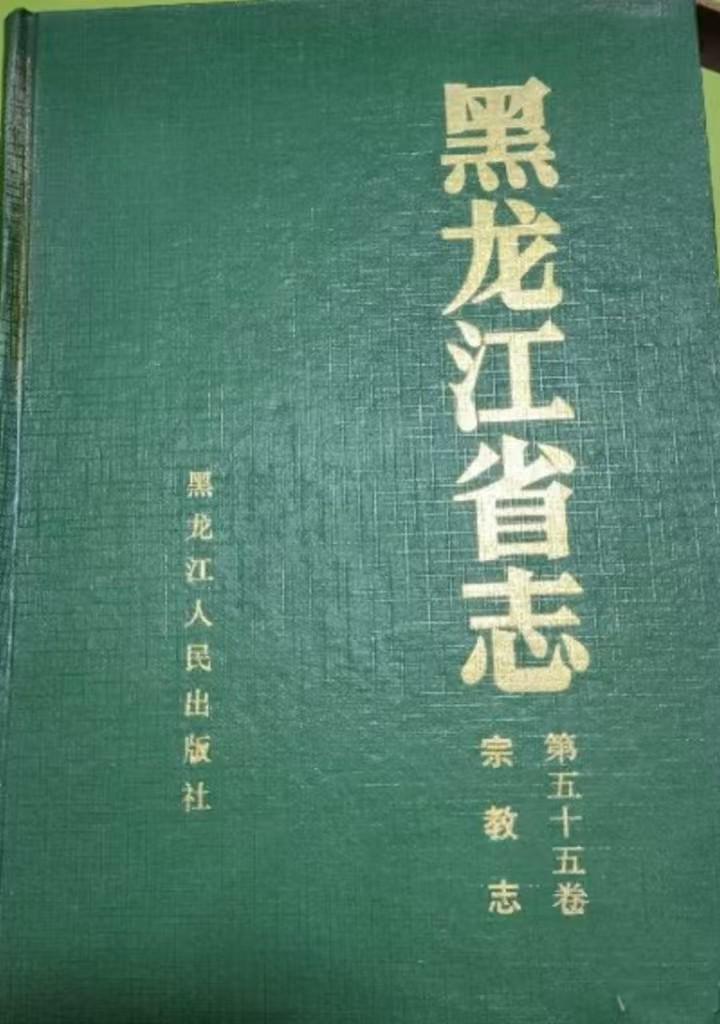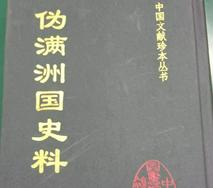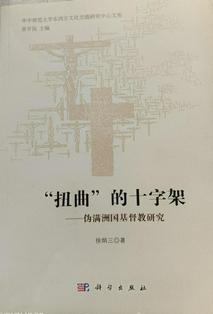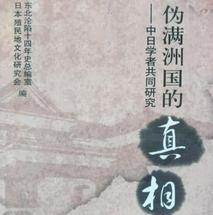问候亲爱的读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这个题目。
六、当时日本基督教界对侵华战争的态度
那么,同为基督教的日本基督教对于政府的侵略是什么态度呢?我们不要以为当时的日本基督教界就真的全部都是有彼此相爱的信仰,他们的主流(我们这里说的是“主流”,因为还有部分有正义感的教会组织和基督徒是反战的,后面我们会介绍)还是为日本的侵略摇旗呐喊、助纣为虐的。日本基督教的主流派在“九一八”后对中国采取了强硬路线,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统治是“神的意志”,并将其解释为一种“教化”行为。
从日本基督教在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的活动来看,其信仰本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日本宗教,包括基督教本身具有明确的为本国政治利益服务的宗旨,因为日本的“海外开教”是带着征服其他民族的顽固信念而来的,因此,其布教使活动必然受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制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必然自觉地配合其侵略行为。第二,世界各民族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化中国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完全以战胜者自居,主宰中国东北民众,企图将自己的生活模式、宗教信仰强加于人,实行殖民地统治。其多数的基督徒和教会也是这种“大日本”居高临下的态度。第三,日本到中国东北的“传道人”中信仰不虔者居多,“吃教”“借教”的现象极为普遍,其中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不在少数,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打着基督教信仰的旗号,专事欺压中国民众,谋取私利,更增加日本宗教的侵略性。
提到日寇在东北的“布教使”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因为在本文中还会陆续出现。
日本布教使分为随军布教和慰问布教两种形式。随军布教是指教团派遣教使与前线军队共同行动,向前线士兵宣教及配合军队从事其他活动;慰问布教则是前往军队驻地,宣讲佛法、教义和赠送慰问物品。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布教使活动是日本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利用宗教手段,试图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控制和渗透。
这里号称“国中之国”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在东北对基督教宗教活动的迫害,更是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殖民教化,对于这个在东北横行霸道的满铁,笔者写了近二万字,今天不在这里赘述,只是最为简单的说一下:南满铁调查部协助日伪方面的礼教课和警务厅特高课,定期对东北全境的宗教团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或典型局部抽查。这些调查几乎涉及了东北所有教派团体及其规模、性质、习惯、布教场所、政治倾向等,并提出具体的对付办法。(参见[日]《真宗》第436号,1937年12月;转引自[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2025/02/0411》2000年第3期,第27页。)
正如前述,日本基督教会在侵华战争初期虽然在宗教理念的促动下发表了和平言论,并为此付出努力,但他们并未认清事实真相,他们内心还是真正认同的还是日本政府的宣传。因此,一旦中日宣战,日本教会主流就会迅速转向日本政府一边,卢沟桥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即是日本基督教界战争态度变化的转折点。比如,部分日本基督教人士宣扬“日本式基督教”,强调基督教与日本民族主义的结合,甚至发展出“兴亚神学”“大东亚神学”,将日本的侵略行为合理化。这两种“神学”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其核心内容是将基督教教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相结合,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提供“宗教合理性”和“精神支持”。
以下是当时日本基督教的“神学”观点。
“兴亚神学”观点:主张日本的侵略行为是“神的使命”,认为日本被“创造神所嘱托”,肩负着“解放亚洲”、对抗欧美列强压迫的神圣职责。这种神学将日本的军事扩张描述为一种“正义之战”,声称日本的目的是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或“大东亚共荣圈”,以实现亚洲的“解放”和“复兴”。
“大东亚神学”观点:进一步强调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神的旨意”,旨在通过“圣战”消灭“邪恶势力”,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新秩序”。
这是对基督教教义的严重歪曲和背叛,它们还试图将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的普遍性相结合,形成一种“日本式基督教”,强调日本基督教的“优越性”,并将其作为“教化”亚洲其他国家的工具。例如,在日本基督教界有影响的黑崎幸吉在其著作《武士道基督教》中,更是荒唐的将武士道精神与基督教相结合,认为日本人在战争中履行的是“神之鞭的使命”,批判英美的政治罪恶,却忽视了日本自身的侵略行为。
当然战后他深刻反思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承认其在战争期间的判断是错误的,并感到羞愧。他意识到日本军部的暴力主义和侵略行为的罪恶,并对日本基督教在战争中的角色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也算是认罪悔改吧。
1937年7月22日,就在卢沟桥战争爆发半个月后,日本基督教联盟(简称日基)发表《非常时局有关声明》,该声明包含四个要点:“(1)值此图谋国民精神的作兴之际,念及吾等基督徒之责任不轻,须更加努力。(2)为了对吾皇军将兵的劳苦表示谢意,而开始慰问事业。(3)希冀以最低限的牺牲早日解决时艰。(4)盼望以是作为一期永久的亲善关系能够得以建立,在此切望全国基督徒热诚的祈祷。”继此声明之后,日本基督教联盟又分别于9月15日和11月24日发表补充声明,三者构成日本基督教联盟对卢沟桥事变意见的宣言。这三份声明完全肯定了日本侵华的“正当性”,并出现“日支(中国)提携共荣”“亲善协作”“排斥无神无灵魂的唯物思想”等字样,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政府更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与动员力度,1937年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提出“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三大目标,并期待基督教团体在内政外交上予以协助。“日基”还于1939年提出《基督教针对国民精神新展开基本方针的强化实施案》,对于政府鼓吹的所谓“确立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联合”的“东亚新秩序”,表示“基于基督教之确信,要为此而努力”,并提出有助于新秩序的各项具体措施。
1940年11月,日基召开庆祝“皇纪2600年”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会,号召基督徒积极致力于建立“八一宇”的“大东亚新秩序”,并在宣言中明确表示“吾等期待完成全基督教会之合一”。此后,“合一”进展顺利,终于在1941年6月24—25日34个宗派召开日本基督教团成立大会,会上315名教会领袖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遥拜皇宫,为战殁者默祷,并宣誓效忠天皇制国家。会议选出富田满任“统理者”。(以上参见日本基督教团宣教研究所教团史料编纂室:《日本基督教团史资料集》,第1卷,土肥昭夫著:《日本基督教新教史》,东京:新教出版社,1980年等)
这说明日本基督教联盟已经接受日本政府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反对共产主义等理论;而声明号召日本教会慰问日本军队、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精神作兴运动”等运动,表明日本教会在行动上开始协助日本政府侵华。同年12月,松山常次郎(1920年,他作为政友会候选人当选众议院议员,此后共当选7次,直至1945年。他在1936年担任广田弘毅内阁的外务参与官,1940年担任米内光政内阁的海军政务次官。二战后,松山常次郎被认定为战犯)、海老泽亮、小崎道雄、阿部义宗等日本基督教联盟各加盟教派领袖45人,联名发表《致世界各国基督教指导者的开书》,称中国政府侮日抗日、容忍共产党、支持反宗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威胁日本国本,是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中国和世界各国基督教领袖当与日本教会一起,维护“中日亲善”“提携共荣”。显然这是一封为日本辩护的文书,是对正义的背叛。除日本基督教联盟外,日本其他基督教教派也纷纷发表支持战争的言论,如日本组合教会曾发出《支那事变有关声明》和《处于时局的协议》,其论调大体与日本基督教联盟一致;而日本圣公会甚至公开宣称“此次事变是圣战”,为日本侵华提供宗教依据。至此,日本基督教界倒向日本侵略势力,逐步滑向军国主义深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宗教随着日军的战火蔓延各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各沦陷区日本教会均与日军如影随形。此时的日本宗教将建成“大东亚新秩序”“圣战完遂”视为己任,宗教传播的目的早已退居其次。日本基督教教会在中国设立东亚传道会,传教范围遍及各个沦陷区。1942年,日本基督教团设立东亚局,统筹谋划传教事务。东亚局有决定各海外传教区长和传教士资质的权力,并对布教区内教会、传道所和原住民传教区进行管理。东亚局向各地教会发出所谓“圣战完遂”指导方针,要求教会昂扬战意、贯彻大东亚共同宣言精神。对于朝鲜教派,日本基督教团力促其联合。朝鲜牧师须经日本基督教团训练,系统学习日本精神史、宗教团体法、日本基督教团规则等内容后,方可取得传教资质。这是因为当时朝鲜在东北有相当多的教会组织。教团试图联合日本、中国东北和华北沦陷区的基督教会,系统掌控沦陷区宗教。教团还建立了所谓的东亚基督教文化后援会,协助沦陷区传教和社会控制,具体措施包括:指导传道工作,安抚各沦陷区;强化教会学校、孤儿院、医院等社会事业,增设新的文化设施:派遣日本教授到沦陷区讲学,援助沦陷区学生赴日留学;资助各地传教士回国修养等。文化后援会所需资金,除少量来自日本外,绝大部分从沦陷区募集。日本还尝试推动日本基督徒向沦陷区移民,为此曾组建“满洲基督教开拓团”。开拓团曾有两批:第一批进驻东北的时间为1941年2月,包括坭并顺次为团长的日本基督徒二百余人,在哈尔滨郊外的长岭子垦荒殖民,战败后回国102人,死亡46人,余者下落不明;第二批是在1945年3月,团长为室野玄一,成员只有11人,开发地为桦川县大平镇,其中5人死亡,6人回国。开拓团成员虽然以基督教名义来到东北,却并从事过传教活动,他们只是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牺牲品。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武力扩张,日本基督教界迎合其侵华政策,在配合日寇对中国东北的军事侵略中从事了大量的宗教活动,对侵华战争,难辞其咎。“二战”结束后,日本宗教界的大部分宗派进行了诚心的忏悔,但仍然有少数教派鼓吹、美化侵华战争。日本基督教派别中仍然有人以“教派个体或者个人”的身份来华“传播福音”,否认侵略战争。
客观公正地说,当时确实有少数日本传教士在东北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热心传教,付出了巨大牺牲,获得了部分当地民众的认可,如承德教区的十永见爱臧夫妇及两个女儿都病死在东北。但是,个别传教牧师的善举既不能掩盖也无法抹杀其他许多人的目的: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这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
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的日本教会最具代表性的和平组织是唯爱社:该社一贯持有和平主义主张, 在“九一八”后即发表强烈反对武力的声明, 号召日本外务部大臣、主要报纸的编辑和中国大臣共同推动危机的和平解决。在1932 年唯爱社决议中有如下字句: “我们日本唯爱社的成员重申巴黎协定, 包括‘谴责’‘诉诸战争’ , 并‘拒绝将它作为国家政策’, 进一步讲,‘所有争端,无论什么特征,永远不能寻求战争以外的解决手段’; 此外,我们还号召中日基督徒去影响各自的政府, 促使政府遵守九国公约和巴黎协定庄严的惯例,禁止使用暴力, 寻求用‘和平手段’解决满洲问题。”部分日本基督徒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如日本基督教思想家吉野造作(1878年1月29日—1933年3月18日),日本大正至昭和前期著名政治学者、思想家,因倡导“民本主义”而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在“九一八”后曾发表大量言论, 严厉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呼吁和平解决危机。其言论气势凌厉, 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贺川丰彦(1888年—1960年)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著名的社会运动家、基督教传教士、作家和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社会改革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实践。贺川丰彦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他曾多次来华布道,关注中日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冲突,并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他的和平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理念在中国教会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多次因反战遭到逮捕和审查。贺川丰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美国华盛顿大教堂立有他的雕像,以纪念他对社会改革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贡献。他连续两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47年和1948年),并在1954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另一日本基督徒曾致信中国教会: “我无话可说, 但我对我们对你们所犯的巨大错误表示歉意。有许多日本人强烈反对这种错误, 并且努力改变公众的观点和促使我们政府撤军, 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一些人甚至敢于直斥日本暴行:“日本确实是军国主义啊, 如果我们不反省和悔悟, 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战后,日本有的教会为他们战时所犯的罪痛加忏悔,如1995年日本福音同盟(JEA)所属教会联合发表《关于日本教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罪责悔改书》,一开始便直言:“我们日本教会曾经在国家神道体制下,以天皇为现人神,犯了拜偶像的罪。”由此可见日本教会希望的曙光。
在揭露日寇在伪满洲国时期对东北基督教的控制和迫害,山下永幸这个名字多次出现,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罪恶多端的人、伪基督徒。
据介绍,山下永幸其实就是一个日军的军曹,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成为日本基督教长老会“牧师”,他在东北的行径说明他没有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其行为更多是出于日本侵华政治和殖民目的,而非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敌基督者。他在“满洲国”时期对东北基督教进行了深度控制和改造,其主要活动包括:
1.对东北基督教会的组织建立与掌控
他创建了满洲基督教会为侵略服务。1933年9月,山下永幸与日匹信亮在东京组建满洲基督教会,开始向东北的中国人传教。该教会很快发展为南满、北满和热河三个教区,到1938年,三个教区下辖教会已达15个。
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6年12月1日,山下永幸推动成立了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并自任总干事。联合会表面上由英国传教士胡成国任会长,但山下永幸掌握实权。该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对东北基督教的统一控制开始形成。
他蓄谋搞起推动教会合并与改造的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下永幸回国,但其建立的组织架构和控制模式继续发挥作用。1942年3月,日本人石川四郎在长春组建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将东北基督教15个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除外)合并,划分8个教区,本部设在长春。这一举措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对东北基督教的全面控制。
2.将东北基督教与日寇侵华政治的结合
山下永幸通过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等组织,宣传日本殖民思想,大力鼓吹“东亚都应顺服日本的领导”“日满华同文同种,必须一德一心”等反动理论。他还推动在基督教活动中加入遥拜日伪“皇帝”皇帝、“皇城”,唱日伪“国歌”,升日伪“国旗”等内容。
山下永幸等日本基督教宗教人士试图将日本神道与基督教相结合,推动“信仰统一”为日本长老宗,“思想统一”于日本天照大神之下。这种融合试图消除基督教与日本殖民政策之间的冲突,使基督教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
3.对西方教会在东北传教的打压
限制西方传教士活动:山下永幸通过与日伪政权合作,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限制和监控。在日伪政权的打压下,西方传教士的活动空间被严重压缩,许多传教士被软禁或驱逐出境。
4.在山下永幸等人的推动下,东北基督教的教会财产逐渐被日本人控制的组织“接受”。
例如,1941年12月,石川四郎与被日伪关押的英国传教士邱树基和方德立订立合同,将教会所有房地产和部分资金移交给临时措置委员会。
山下永幸的行为更多是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和对殖民利益的追求,而非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他的活动不仅没有体现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如爱与和平,反而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一部分。这种行为与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山下永幸虽然拥有牧师的身份,但他更多是将基督教作为实现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而非真正践行基督教的信仰和价值观。将东北基督教改造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严重扭曲了基督教的本意,也给东北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