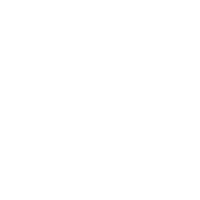对于洛桑运动,笔者主要摘读了两份文件,一个是J. D. Douglas编辑的《让全球听见祂的声音:瑞士洛桑世界福音国际会议官方文献》,一个是C. René Padilla编辑的《福音新面孔:关于洛桑信约的国际座谈会》。洛桑运动要比笔者过去的听闻有意思的多。1974洛桑会议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主要由美国福音派主导,仅能看到两个华人名字:章力生和赵天恩。(这两个人都是海外华人,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时期。这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直到今天,大陆福音-灵恩派的状况总是被海外华人所代言,并且主要是北美。)
在《洛桑信约》签署后,“超过五百人在大会的周日晚上聚会,讨论‘当今激进门训的社会和政治实施’,一个小组筹备了一个简短文件《回应洛桑》(以《激进门训的神学和实践(Theology and Implications of Radical Discipleship)》为题收录在《洛桑官方文献》中),他们认为《洛桑信约》走的不够远。”(Padilla, 91页)两年后,这个小组的两个领袖——来自阿根廷的C. René Padilla和加拿大的Samuel Escobar召集了一个特别的国际座谈会逐条回应《洛桑信约》。结果就是《福音派的新面孔》,赵天恩犀利的《教育与领袖》就包含在其中。让我们来摘读赵天恩的这篇文章:
除非《洛桑信约》的观念被落实,否则没有价值……第三世界福音派需要从西方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尤其是盎格鲁-美国人的福音牢笼……实践于大多数第三世界教会的新教事工模式基本上是西方教会史处境中建立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事工模式……这种从西方进口的模式是天主教或圣公会教区或聚会的全职专业牧师;神学学校的目标是宣教士指导和收费式的培训牧师或传道人……福音派过分重视宣教,热衷于报道“教会增长”的数据成功,产生出低廉门训的表面福音……宣教学校经常贬低民族文化遗产,这样通过西化的驯养,将学生从他们文化背景中剥离了出来……很多西方的宣教机构拥有意识形态和行政上的最终话语权,他们并不免疫于剥削实践……在培养合适的本土领袖方面,所有的宣教都失败了……通过从西方出口的传统事工宣教模式的批判历史分析,表明它是建立在反映罗马心态的行政结构上,而不是新约中所教导的服事功能结构……第三世界神学教育应该遵循圣经和本土路线发展,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神学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拒绝自由-保守或普世-福音这样的二元论……如果我们质疑有偿牧师事工牧师,我们就需要发展出协调于全身事工模式的规划……这意味着现有秩序基础的震动和崩塌,会有很大的代价……在宗教改革中就牺牲了不少生命……创新者会被宣教士和同工所误解,因为他们还没有从攀附心理中解放出来。但是第三世界的神学领袖们是时候联合起来,在神学解放运动中形成统一战线,这个声音已经在洛桑的激进门训小组会议上听到了。(Padilla, 194-204)
但是赵天恩期许的神学解放运动今天看起来失败了,并没有出现神学解放运动,至少在大陆是这样(也许他的福音派式异象在南美洲的解放神学中有贡献,但是在东亚尤其是在大陆看不到。如果说大陆的神学建设,倒是官方教会领袖丁光训等可圈可点,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其中原因笔者认为是福音派神学思辨方面的欠缺。现在很多国际神学院是很尊重和推崇各国文化的,但是文化与文明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如果前者是处境层次的对话,那么后者是文本层次的对话。就是,当你拿出圣经文本时,在文化层次的服饰、饮食、文字等方面上相对容易应对,但是在与圣经成书历史相平行的其他文明层次上,比如儒家、佛教典籍,怎样应对。
保守福音派具有宣教实用性,有时我们可以说它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从神学方面,它是典型的拉丁传统,就是创造-堕落-救赎的程式。从宣教角度,它是经典的教会栽植模式,就像101-201-301课程程式一样。这具有很高的效率,至少在较短历史期间的教会成员数目增长方面是这样的。在这种路径下,宣教士不需要辩证思想,辩证思想甚至阻碍这种宣教程式,也会被教会领袖所奚落。
保守福音派宣教士经常造就出福音机器人。有时这些作者倾向于生活于胜利主义的幻象中。尤其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姿态,潜意识中有种宗教进化论。作者经常生活在一种完美假象中,比如当约翰·派博强调殉道的价值时,他自己从来没有行动过。他就像战场上的一位指挥官在发号施令,而自己站在一个安全的堡垒内。笔者对比过保守福音派与贵格会的教牧事奉书籍,保守福音派总是喜欢讲自己医治了别而贵格会讲述自己怎样别被别人医治。对我来说贵格会总是比保守派要靠谱。
相比于一些亚洲神学家安炳茂、宋泉盛、丁光训等,笔者将保守福音派的立场放在“教会的拉丁俘虏化”(虽然赵天恩虽然从历史族群角度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拉丁传统”这样的神学专业词汇并没有看到,看不到他在神学上有任何突破)。在近代主流教会方面,由于拉丁世界的全球殖民,拉丁传统几乎垄断了基督教的话语权,并且将福音简化、弱化为信徒身份的数字化。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新教继承的仍然是拉丁传统的核心教条,比如奥古斯丁主义,而完全边缘化了其他的传统如希腊神学传统。
如果我们打开视野,我们会看到东西方教会如此的不同。(顺便提一句,在本文中,西方教会包括天主教会和新教等,而东方教会包括东正教和景教等。)首先,在东方传统中,父神一般被视为等同于古兰经中的安拉,而在西方传统中,安拉总是被拒绝。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东欧东正教总是可以与穆斯林和平共处——另外我们应该尊重历史,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徒处境并不比宗教改革时期异议基督徒的处境差,尤其是激进改革派遭受的屠杀。圣经中的神与古兰经中的安拉——还有在其他宗教和文化中的其他神名——是传教时的一个核心问题。(讽刺的是,英文上帝God来自于异教文化。)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内容而不是名字本身。
现在让我们转向耶稣的名字和内容关系----在神学中我们经常称这个内容为耶稣的“工”或具体的“生命”。在使徒书信中只有耶稣的钉死和复活,至于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不再提了。更加明显的争论是,现在的教会更像是耶稣的,还是更像是保罗的。我们能够发现福音书与使徒书信之间很多不同的导向。比如,在福音书中对于以色列,耶稣聚焦于审判它,而使徒书信聚焦于复兴它,比如保守宣教学喜欢引用罗马书11:25-26以色列全家得救作为宣教的目标。(Piper,223页)另外,保罗完全将救恩论放在法庭和原罪审判的场景下,而在福音书中耶稣更喜欢光——而实际上他就是光,就像希腊传统的救恩论更强调光亮一样。
笔者想问的一个问题是——笔者想其他人也问过——保罗完全知道了耶稣吗?(有人拿耶稣是射出的起点,保罗是射出的轨迹来形容他们的宗教关系。但是我想用另一个比喻可能更加恰当:耶稣是光源,保罗是其中一道光束,但是不仅仅有这一道光束。)我想我们可以说他在他的处境和背景下体会、跟随、活出了耶稣基督,这包括他的犹太人身份、罗马公民、以及当时政治的动荡不安,等等。
整体上,笔者认同安炳茂、宋泉盛等对上帝使命(Missio Dei)的定义,就是上帝使命从起初就临在于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中。另外民众基督论可能解决了关于耶稣基督人性先存性(preexistence)这个最艰深的神学问题。这个路径跳出了线性救恩史的藩篱,启示出超历史或原史(德语:Urgeschichte)。宣教的使命不仅仅是栽植教会,而更是要在自己的文化历史中发现基督的临在。事实上,从中国古典典籍中,笔者总能发现基督化或圣经化经文。如果我们否定普遍启示,就是否定耶稣基督的永恒性。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定义福音,我们并不是将福音带给未开化者(unreached),而是揭示已经临在于他们中的上帝。
悲剧的是我们人类总是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观念认定为上帝使命强加于人。这就是为什么近代基督教总是被指控为殖民主义和侵略(确实殖民主义主要发源于拉丁传统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除非非拉丁文化中的本土基督徒在他们自己已有的文化历史中揭示基督,否则基督教总是沉沦成一种殖民文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赵天恩以及其海内外众门徒所期许的“激进门训”式的“和平演变”在中国大陆一事无成。我们必须尊重上帝在不同国家、民族、宗教和历史中的文明和文化表达的多样性。
参考书目:
Wright, Christopher J. H. 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Church’s Miss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2010.
Douglas, J. D., edited.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Lausanne Switzerland. Official Reference Volume (《让全球听见祂的声音:瑞士洛桑世界福音国际会议官方文献》). Minneapolis, Minnesota: World Wild Publications, 1975
Padilla, C. René, edited. The New Face of Evangelical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Lausanne Covenant (《福音新面孔:关于洛桑信约的国际座谈会》).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1976.
Piper, John.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The Supremacy of God in Mission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s, 1993.
(注:本文原载于“信仰和学术”公众号,福音时报蒙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