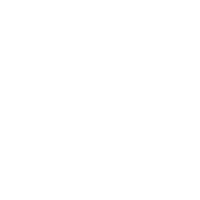忻若的梦境切换着,她感到自己一会儿蹲在亓山河边,一会儿漂浮在橘园的上空,一会儿走进树魂的梦境。树们都在橘园上空的云层里漂飞着,它们都在拼命结果子,结了许多许多。葡萄蔓们连根带叶地在云间飞舞,晶莹的葡萄一串串挂满枝头。柑树和橘树们挽着果实累累的枝头围着无花果树翩翩起舞,它们是来让主人品尝果子的。
树们边舞边唱:“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树们慢悠悠、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跳着。亓山也走了上来,它跟着节拍,轻摇着它那笨乎乎的身躯。忻若看到屋边亭和黄杨山居就在云间,家人们进进出出;大方桌搬了出来,架在云层和许多树根交织起来的平台上。一只塑鸟在禇老先生旁边飞来飞去,它唧唧啾啾地唱着“主人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器.....”。
“你不是补过尾巴的那一只吗?你怎么把赞美诗改了!忻若对小塑鸟笑着说。
树们把最好的果子送到桌上,金灿灿的、绿莹莹的,摆满了一桌。“主人终于开始吃我们结的果实了,这么多年来主人还是第一回尝鲜呢!”柑树和橘树受宠若惊地说。“吃吧,吃吧!这回不用等谁了。”树们兴奋地摇摆着身子说。
树们不断地结果子,又不断开花,欣若分不清是秋天还是春天。“这是我们的春天!”有声音从石狮脚边传过来。“你起得好早啊,蜥蜴王子!”石狮说着,一边揉着它那惺忪的睡眼,一边在漂浮的石块和泥土上溜达、伸腿。柔和的阳光从亓山后边溜过来,飘动的草丛上露珠闪烁。蜥蜴从石缝底下探出头、张着嘴、吐出芯子等待猎物。青泥塑鸟们别着脖子蹲在花瓶上酣睡着,它们在做着被塑造、被精雕细琢、被修复尾巴的梦“快醒一醒吧!”蜥蜴一边说一边舔着嘴角的虫汁。
“好热啊!别烧我们了……”一只名叫素素的塑鸟说着梦话,它梦见自己和伙伴们被送进瓦窑,与瓦片砖头一起被烧制,及至出来时几个被碰掉了尾尖,有的嘴巴被碰掉一块的情景。特别是那惊心动魄的‘火炼’那是获得新生的的过程啊!“老园丁真好,他在泥花瓶上把我们做成花瓶上的饰物,送我们进火窑——炼炉,从此换一副硬骨。他把我们彻底修复,要不我们非得成为残疾鸟才怪呢!”小素素说着下意识地用小嘴梳理一下自己的尾巴。“只有他才能把我们修好,不过,不修好也就白白塑造我们了……”塑鸟们,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它们唱起了自己改编的《窑匠与泥器》歌。“既然那么爱戴他老人家为什么不去陪伴他呢?”石狮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说。“我们飞不了那么远只好在橘园上空盘旋,再说,我们也不想离开相依为命的花瓶呀!本来先生就是把我们塑造在花瓶上的。”塑鸟们理直气壮地说。
“石狮大哥,各有各的难处,为难它们也没有用。橘园虽已没有了,可它却在我们的记忆里,梦里永存。梦里有橘园,梦里就有老先生。自从橘园消失,园里面的一切都成为精灵。一草一木,泥塑的,石雕的,都有了灵气。别看蜥蜴和我都在吃着虫子,其实我们都在咀嚼着虫子的精灵。”躲在耳朵草底下嚼虫子的一只青蛙一口气说了一大通。
太阳已高过山顶,酸咪花仰起脖子向着蓝天绽开小小的花朵。酸咪草也张开它那三瓣莲花叶,绿的酸咪草与红的酸咪花一组组、一对对围着蜥蜴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它们牵着蜥蜴的手称赞它,称它为蜥蜴王子,因为它与众不同有一对一大一小的尾巴。那是小主人不小心踩断之后长出来的,蜥蜴感到幸福无比,精灵们都羡慕它,都说那是受主人宠爱的标志。蜥蜴有点飘飘然“昨天还不是这样的……”蜥蜴喃喃自语。望着满园的春花笑意,蜥蜴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舒心,它身上每一张鳞片都洋溢着欣喜。
梦境又切换了,那是梦境里的夜。无星、无云,照亮园子的是银光闪闪的葡萄叶。欣若走进葡萄与柑橘的梦,她走向飞舞的葡萄树,惊叹着、欢呼着。葡萄树们或停在半空或立在云头,它们枝躯相拥着,叶片厮磨着,组成了飘动的葡萄园。蜜柑与黄岩橘树向欣若伸出新枝,在她手心里开花,结出果子。欣若把一瓣蜜柑递给石狮,他们一起品尝着甜蜜蜜的果子。树和果子们都笑了,“看着主人全家在品尝果实,我们幸福极了,吃吧!吃吧!盼了多少年,盼的就是这一天!”树们不约而同地说。那是狂风暴雨的岁月,也是希望与期盼同在的日子。春花带来了希望,寄托着期盼。秋实连同愿望装进坛坛罐罐,等待团聚时品尝,直到果子烂去,又是来年春花秋实。年复一年直到橘园消失……
苧们好久没有修整过了,它们懒洋洋地挤在一起,做着躺在河里浸泡的梦,做着鱼儿在身边穿梭、大小船只往来经过的梦。它们看到一捆捆麻线、麻团整整齐齐地排在小船上。“这是运到大墙后的麻厂的,那是运往水乡湾塘的。”苎们指指点点地说。浪花打在河埠台上,水花溅到浣衣女的裤管上。苧们笑了,它们在船浪里荡漾,主人们还让它们在河里翻几个跟头。
在葡萄园里,苧们一根根躺在主人的手心里,被分成三种物体,苧丝、苧皮、苧梗。苧们都很乐意成为有用的苧丝,它们排着队翘着首等待着,望着晾晒在竹竿上那雪白发亮的苧丝,苧们都赞叹不已。从苧株到苧丝,是一种快乐的过程,在苧们的生涯里,每年有三次这样的快乐时刻。“几十年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苧们喃喃梦呓着。“苧们又做梦了!”老无花果树同情地说。
苎们在飘动的苎园里挥动着叶子向忻若招呼,“来看看我们吧!来看看我们吧!”明月如镜、似水,苎叶们挨个抚摩着欣若的脸,硕大的无花果在枝头向欣若微笑。
“你怎么也来了?也来看苧?找寻无花果?抑或只是瞧瞧凉棚刺刺?”欣若对头顶的月亮说。
“也听听苧们的歌。”月儿说。
苧们真的唱起来了“我们被栽种在高过橘园的山地与亓山相连,是橘园里的一片。我们守卫在边缘,与刺丛连成一片。我们占的只是些石头地,把好地都留给无花果。我们与无花果树组成苧园,也叫做‘山里’。我们更喜欢‘苧园’,它亲切。我们爱听被叫做‘苧园里的苧’,这里的无花果喜欢把他们叫做‘苧园里的无花果’。”
“别了,飞舞的树!香甜的果!别了,我的苧麻、刺丛、无花果!”欣若似醒非醒地走出了梦境中的梦境,走出了梦里的沉思。
“也看看我们嘛!”山边大墙上的紫茅、卷枝、刺藤、首乌、乌子儿、红算子们伸出枝叶可怜楚楚地说。“它们还是那样亲切可爱的样子!”欣若说着向大墙与小屋走去。那里有一间叫做小屋堂的木板屋子,屋檐上还爬着当年的葡萄蔓,瓦片上依然躺着葡萄串串。欣若走近小屋堂,还是那些条壁、木门、石板台阶。踏进小屋,欣若看到一盆盆花,一篮篮干无花果“好香!这不是梦?”她喃喃自问。
忻若每次梦回橘园总要来看看这间小屋堂,还有那堵与它相连的大墙,原先它们只是堆放杂物的小木屋和长满杂草的石墙。“在梦里它们却是如此的美,这么地富有诗意,就连那讨厌的卷枝藤都变得亲切可爱了。“啊!我的大墙,我的小屋堂,我的身影,我的梦乡!”欣若终于醒了。
主人栽培这些果树已多年了,尚未尝它们结的果实,是因为主人的美好愿望未实现。这些被主人叫做蜜柑与黄岩橘的果子年年被主人珍藏着,说是等全家团聚时吃。直到一个个烂掉,就这样一年一年等下去。
树们一点也不抱怨,它们理解主人,支持主人。“到几时尝都无所谓,只要自己年年结果主人总会尝到的!”,树们心里想。树们愿意替主人分忧解愁,它们茂密的枝叶以及年复一年的春花秋实使主人的盼望有所寄托。
长辈们在盼望里安息了,晚辈们仍在盼望里期待,树们坚持不懈地结果,等待主人们围着它们尝新的日子……
树们守着小主人,白天它们忍受着外来的侵扰和欺凌,夜深人静时它们就做着“主人围着它们尝鲜的美梦”。树们已被蹂躏得断枝残干,眼看主人家的欢聚日子就要到来,树们聚集全身的养分才结出几个小果。它们除了尽力哺育这几个小果之外,还在梦里不断地鼓励小主人说:“快了,快了,耐心等待吧!”
树们还是被铲除了,一大片“楼林”占据了树们多年生息的土地,树们没有了树身,只有一丝飘飞的树魂。树们只有在云层里做着为主人开花结果的梦,做着主人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的好梦!
亓街变得认不出来了,临街房子,还有在橘园里建起来的居民楼及亓山周边的一切房子都被推倒了,河道正在加宽加深,路面也挖了,这里要进行景观大改造。忻若走在瓦砾上,一边回味着梦中那些飞舞的结果与不结果的树,还有那些快乐飞奔的生灵。那些原先生长或摆放在橘园里的一切都有了生命,泥鸟、石狮,打造的、塑出来的、自生自长的,它们在飞舞的树与飘动的草间欢快地穿梭、栖息。
“这里应该是黄杨山居与屋边亭,左右外围是邻居们的房子;这边向东延伸直到亓山脚中间,加上那边向左延伸,再向东拐弯直到亓山东头是原先的橘园。再扩大三倍,又是上一回梦中的橘园……”,忻若用脚丈量着、估摸着。
“梦真好!在梦里连犹大都能悔改!梦中的一家多和美啊!”,忻若走着、想着、被前前后后的梦境陶醉着。梦里有黄杨,有月月红,有原先的、被她叫做黄杨山居的故居;有早已没有了的屋边亭;有无泥无土、无任何干扰、远离尘嚣、漂飞在空中的永远的橘园;有富丽幽雅的超大橘园和改建成画廊的叫做黄杨阁的故居。在梦里那条已变成了臭水沟的亓山河又是繁忙而美丽的水道;在梦里已故的亲人快乐地生活在自己身边;在梦里犹大还有一个学美术的儿子,就是与老夫人一起在老先生书房里看作画、帮忙的那个“表弟”;在梦里不只是忻若一家人实现了美好的愿望,连橘园里的树们都实现了它们苦苦期待的愿望;在梦境里橘园永恒了,树们和万物也永生了。
望着一片废墟,忻若思绪万千,梦境连绵。现实与梦境交织着,她想起她以前写的歌:“我流浪在异乡,走过一庄又庄……”是啊!她忻若只是回来看看的,她想到她两天前刚刚去过的出生地,那里有一间叫做“被虏之地暂作圣所”的小屋子,那是忻若姐弟与他们父母住过的地方。
忻若几十年没有去看那个他们家住的屋边就有水井的小屋子了。这个小屋子之所以被叫做“被虏之地暂作圣所”,是由于应了“约柜被虏到大滚庙”这个典故,因为在他们搬来之前,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小庙宇。
一想到那个地方,忻若又晕乎乎、梦兮兮地,犹如回到了她的童年,她感到自己又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爸爸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他穿了一件衬衫,这衬衫还是当年那件他常穿的有暗花的白衬衣......”忻若激动得喃喃自语。她向她的妈妈、她的姐姐、她的弟弟走过去。她妈妈把她抱在身上,六岁的她与三岁的弟弟分坐他们妈妈的腿,一边一个。
往事涌现在忻若的脑海,她记得有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这人与她父亲谈论了好久,那人临走时她父亲礼貌地说一声:“再见!”那人说:“高墙内见!”
没过几天忻若一家就见不到父亲了,“高墙”那边有话传来说,只要他们父亲答应不再信上帝就可以立刻回家。
“高墙”就在巷子里面,与忻若家屋边的水井隔路相对,一直延伸到巷底。那边的墙面有一扇小门,门对面又是一个水井,门口有士兵守着,有许多干瘦如柴的男子挑着水桶出来挑水。一看到那边开着门,忻若那三岁的弟弟就哭着往里冲,“我要看爸爸!我要看爸爸!”
他们是从当地安息日会堂被搬过来的,作为“暂作圣所”,每个安息日还继续做礼拜。“那是凭信心走过来的,是‘过约旦河’!忻若想起她妈妈那时候就是这样说的。
那时候忻若也经常做梦,她梦见自己一家是黄鹂鸟,美丽的鸟父被鹰王抓去做苦工、受欺凌,羽毛变得旧旧的、稀稀拉拉的。一边做苦工,一边要受小鹰和秃鹫们的鞭打、辱骂,每当这时睡梦里伤心又气愤的忻若会喊叫起来:“还我俊美的鸟父!”,“还我俊美的鸟父!”
“‘暂作圣所’被搬到一处又一处,直到美丽、年轻的‘鸟妈妈’也被弄进了那座‘高墙’......‘必须经过!必须经过!’,妈妈总说一切都是必须经过的。是啊!一切该来的谁也挡不住,就如这里,谁也料不到会成为一片废墟一样!”忻若深有感触地想着。
忻若想起小时候与她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她妈妈烧的菜,她妈妈的音容笑貌。那是她与她妈妈住在第二个“暂作圣所”的时候,她妈妈说“圣所一定会归回,这是上帝在异象中亲口说的。”
“二暂圣”只有一小间及一小块厨房,安息日的时候欣若经常被钉在房间里。一大早或聚会一半,她妈妈就被抓走,直到天黑才让回来。家里总被闹得天翻地覆,都是周围的孩子们来闹,闹过之后,地上有时候还会被倒上粪便,然后把门钉死,把欣若一个小小的孩子关在里面。
除了安息日,平时还算平静,忻若有时会缠着她妈妈讲英文,什么星期呀、月份啦,甚至这个bone(骨头)、那个bone。说多了,她妈妈就说“其来(什么什么,gilei)bone,其来(gilei)bone......,因为人的骨头根根有名称,总会记不全的。欣若只觉得听起来好玩,特别是讲到后边,越讲越快的时候。
“二暂圣”附近有小桥、小河,还有公园,穿过公园是一个大水潭,那是洗衣服的好地方,欣若还同她姐姐去那里洗过衣服。后来她们又被搬迁,“三暂圣”是在有很多人家的大院子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十来岁的姐姐总来看她、陪她,甚至来到橘园之后还来看过她,让欣若永远不能忘怀。
忻若还去看过现在的‘暂作圣所’,在那里她与姐弟及各自的孩子、家人参加了当天的安息日聚会,听他们父亲讲道,全家合唱《领进迦南》。来聚会的人很多,摩托车、汽车排满了整整一个院子。那是一个平安、快乐、轻松的安息日,是忻若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安息日。
忻若的思绪切换着,一会儿是一处处的“暂作圣所”,一会儿又是一个个不同的橘园。梦与现实交叠着,废墟与重建过的有点陌生的亓山塔相对着。忻若回忆着过去,想着她的家人,也想她的一个个朋友,临近的阿露、小倩,郊外的安妮,水心的双慕,心园的薇薇。一只小花雀从忻若头顶飞过去,它打断了忻若的思绪。
晨风吹拂着忻若的长发,初升的旭日从亓山后边慢慢爬上来,透过两棵叶儿稀疏的小树照过来,照到忻若那蓝底、粉白与淡紫的碎花绸裙上,断墙上,瓦砾上……
(注:本文节选自陈迦南著作《梦影》,福音时报蒙作者允许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