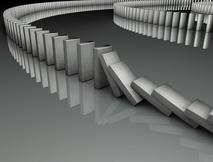西方文化以人们难以预料的方式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文化的焦点从关于现实的真相转移到一场激进的自我表达的竞赛,这场竞赛胜过乃至淹没了其他所有思考。作为主的门徒,基督徒应该如何在这样的文化中生活,又该如何回应我们周围的世界?
Stefan Gustavsson在欧洲领导力论坛大会上做了“自封为王:理解当代文化的混乱”的讲座。在讲座中,Stefan以欧洲当前的文化乱象(主要是与人的身体和性相关的混乱)开篇,挖掘了潜藏在乱象之下影响文化的思想,仔细分析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世俗”和“自我表达”。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离弃神、人自己造神、直到人就是神,其中Stefan提到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以及萨特的哲学。加上弗洛伊德对性的认识,它们共同造就了今日的文化乱象——没有神,个人的自我就是宇宙的中心,而性又是自我的中心。讲座以基督徒的应对结束,Stefan提到澳大利亚神学家所说的四种应对方式,他所赞成的是第四种:帖撒罗尼迦策略,即向这世界宣扬“另有一位王”。
Stefan是欧洲领导力论坛指导委员会成员,一间基督教护教中心的主任,瑞典福音联盟初始以及16年的总干事,居住在斯德哥尔摩。
讲座开篇,Stefan提到近来的一些文化乱象。
几十年有一部电影叫《万世魔星》,有个场景是一群犹太游击队员聚在一起讨论,其中一个男人说,我想当女人,我想生孩子。队长非常沮丧,认为在他本来就不能生孩子的情况为他争取生孩子的权利有什么意义?队里的一个女人说,这象征着我们对压迫的反抗。队长嘟囔,这象征的是对现实的反抗。几十年前,我们尚能因为这个场景的荒谬而放声大笑。
在今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时,立志成为英国下一任女性与平等事务大臣的政治家被问及什么是女性时,她拒绝回答,她拒绝为女人下一个定义,但她却在为女性的权利而奋斗。针对此事,《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在推特上发言,让人给这位政治家寄一本字典和一根脊椎骨。但在社交媒体上随后的辩论中,被批评的显然是罗琳。
瑞典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有关婴儿在出生时被分配性别的文章。好像婴儿的性别是“邪恶”的医生随机做出的选择,说这个是男孩,这个是女孩。
Stefan总结说,和我们的身体和性有关的问题已经成为公共和政治辩论的中心。性已经成为一种新国家宗教的一部分,一种异端被烧死在文化火刑柱上的宗教。
Stefan发出疑问,我们肯定每个人做选择的自由,但我为什么要肯定你的选择?欧洲文化如何陷入今天这种境地的?我们有可能理解这种文化混乱吗?身处其中又该如何应对呢?
Stefan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知道造成今天这种情况的原因。但在开始分析之前,他先做了一个说明。他不认为过去的欧洲是黄金时代,也不想回到过去。前面几个世纪的欧洲也充满了问题,有种族主义、奴隶制度、对女性的剥削、对穷人的压迫,还有遍布欧洲的妓院。过去不是什么都好,但和现在相比,过去的时代人们有个共同的基础,你可以由此出发批评所有恶的事情。你有谈论现实问题的道德基础,因为人们信仰上帝,或者说至少有很多人信仰上帝。作为上帝的创造,你可以用上帝的话语和人们进行理性的沟通,但现在这个基础消失了。我们生活在混乱中,却没有可以批评它的基础。
进入正题,Stefan指出,要理解当今的混乱,需要从能看得见的叶子枝干找到看不见的根。若文化是一棵树,它的生命与形态来自它的根。文化的根是思想,那些起着重要作用的思想,理解滋养文化的思想很重要。这些思想就像一个小雪球,在雪地里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在滚雪球,那在欧洲文化中滚着的雪球是什么?
对不同国家的世界观调查有两个维度,纵轴是传统(宗教)还是世俗,横轴是专注生活环境还是自我表达。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集中在世俗和自我表达这块区域。在世俗的文化中重视自我表达意味着什么?
Stefan用两个要点来说明在文化中滚着的雪球。第一点是“人造的王”(the SELF-MADE king)。在这部分他着重解释了“世俗”这个概念。世俗这个词源自一个和时间有关的拉丁词。世俗的意思是关注这个时间,这个时代,而不是未来的时代。关注这个世界,而不是未来的世界。此时此地,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唯一重要的事,而不是上帝、属灵境况、上帝的国以及即将到来的世代。
欧洲的文化变成世俗的文化,这非常奇怪,也令人惊讶。欧洲到处都是美丽的教堂,塔尖高耸入云,向人们诉说着有另一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塔顶是十字架,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犯罪,上帝也没有抛弃我们,而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重新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家。基督教信仰的象征遍布欧洲大地,但如今它们更像博物馆,因为文化决定与基督教离婚。Stefan认为启蒙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影响。
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在知识层面对基督教的反对。知识层面,人们决定不再信仰上帝,不再信仰基督教,因为它不符合理性。启蒙运动同时也在其他几个层面反对基督教信仰。科学层面,人们说信仰与科学不符,科学驳斥了基督教信仰。历史层面,人们说,圣经讲述了很多历史事件,但其实这些事件并未发生,它们只是神话,是人后来编造的故事。道德层面,人们批评说基督教伦理对人的生命有损,是压迫性的,甚至说如果研究旧约,连上帝本身也是不道德的。制度层面,教会以及教会的等级制度也受到批评。
Stefan认为,面对多方冲击,欧洲基督徒的反应在很多方面都不够充分。一部分基督徒开始认同部分批评,随之调整基督教信仰,删减信仰的部分内容,最终留下的只是人文主义的伦理。另一部分更为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则退回到属灵的庇护所,不关心这些批评,让它们大行其道。总体来说,没有足够的护教学出来解释信仰,为信仰辩护。其实很多批评并没有根据,可以很好地予以回复。总之,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分离,变得世俗化。在欧洲社会取代基督教信仰的世俗的人文主义,人庆祝自己摆脱了上帝、基督教和圣经,体验着自由。人们废黜了真正的国王,为自己造了新的王。
Stefan讲的第二点是“人成为王”(the SELF made king)。他在这部分重点解释了“自我表达”。
在启蒙运动之前,欧洲的哲学家已经开始朝着强调自我的方向发展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罗素、康德、尼采的哲学都把人放在中心的位置。Stefan重点解释了萨特的思想,因为这是最为明显的例子。萨特在他的名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中谈到,过去人们相信上帝,那时人的存在是这样的:上帝在思考要创造什么,他决定要照着他的形像,按着他的样式造人,然后他按着所想的创造了人。上帝决定了人的本质,然后赋予人存在。但是现在没有神了,人也就没有了本质。你不能定义人是什么,我们只是存在,就这样被扔进了世界,没有本质、没有身份。人要给自己一个本质,选择自己成为谁。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观点,但它遵循世俗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的模式:只剩下我自己,我来定义我是谁。这种观点与欧洲的传统观点有巨大差异。
Stefan对比了过去和现在人认识自己的两种不同模式。每个人都有自我,有内在的生命、强烈的情感以及在自己里面进行的争战。但在过去,个体被置于多重背景下。人在家庭中出生,家庭会定义你是谁。同时人出生在一种文化中,而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教会和圣经的教导所定义。在这一切之上,上帝给了一切受造物存在的本质,因为他是创造主。人们生于其中的圈子可能是压迫性的、有破坏性的。家庭可能会压迫个人。文化也可能会压迫个人,因为人们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若是你出生在特定的阶层,一些机会对你来说就是不可能的。这些圈层可能是负面的,但它们确实赋予了一个人意义和身份。人出生在关系和身份中,即便它们并不正确。
现在的情况是人驱逐了上帝——人类生存的终极背景。当然其他圈子还在那里,家庭、文化、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教会,但所有这些背景都变得流动、模糊,不能定义人是什么。个体的自我比这些背景更强大、更重要,整个权威结构都崩溃了,个体自我的表达在带着所有这些圈子前进。
在人需要自己给自己定义的时代,Stefan指出,一些和思想没有直接关联的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它们是技术、商业和政治。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可以打破更多边界和限制,可以在世界各地旅行,和不同地方的人联系。人们可以创造虚拟现实,创造自己想要的世界。商业也迅速发展,不断向人推销新的产品,让人们相信拥有某个产品就能有一个新的身份、一种新的自我表达。一些政治议题,比如全球化的发展,多年来也在朝着尽可能多地消除边界和限制的方向进行。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技术、商业和政治与世俗的自我表达结合,文化逐渐变得疯狂,人的内在自我被提升成为你能想象到的所有领域的终极权威。
过去和现在的不同,Stefan从另一个角度做了说明。所有文化都必须处理善和恶的问题,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中区分方法略有不同。它们可能是有罪和无罪、荣誉和耻辱、纯洁和不洁、力量和软弱,等等,围绕不同的概念所构建的思维方式略有不同。今天的善恶概念是什么?是快乐和痛苦,这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带给我快乐的是善,带给我痛苦的是恶。
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的学说很自然地进入了人的视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非常清晰的一点是,他认为性是定义我们是谁的关键。其作品《文明及其缺憾》一书写到:“爱得以表现自己的形式之一——性爱——使我们最强烈地体验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快感,为我们追求幸福提供了一种模式。还有什么能比我们应该坚持沿着这条我们首次遇到它的道路来寻求幸福更自然的呢?”弗洛伊德认为性的幸福是人类幸福的关键,所以将性与人生命中最基本的方面联系在一起。
所以,人以快乐还是痛苦来区分善恶,而性是人存在最重要的部分。
Stefan认为,他前面分享的这两点共同造成了现在的文化风暴。人离开神,自我成为宇宙的中心,而性又成了自我的中心。
在这个文化风暴中,基督徒该如何自处?基督徒当然愿意主张多元主义,为每个人提供保护,让每个人都有宗教自由,都有形成自己的想法、公开表达自己信仰的权利。但Stefan指出,今天的文化在朝着集权主义的方向发展,不是政治制度上的集权,而是文化上的。你不能自由地思考、决定和表达自己。他认为今天基督徒的处境更像第一批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处境。罗马人将基督徒视为人类的敌人,视为无神论者,因为基督徒不跪拜凯撒。他呼吁基督徒诚实地面对欧洲的情况:基督徒是欧洲新国教的异端。
在应对当前的文化混乱上,Stefan介绍了澳大利亚神学家Michael Byrd的观点。Michael Byrd提出四种应对方法。一是他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被绑架者与绑架他们的人建立了联系。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自由神学就是这样。这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二是本笃会的选择,即面对敌对的文化,基督徒选择退出当前文化建造自己的道德社区,在其间基督徒可以表达所相信的价值观,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这个选择的问题是,在我们所处的现代国家社会中,国家无处不在,你不可能彻底地退出所处的文化。第三种选择是,人们可以期盼出现一位伟大的信仰基督教的政治家来扭转一切。一个人扭转一切,这个希望不大,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要复杂深刻得多,没有任何政治家可以做到这一点。最后一种选择Michael Byrd将它称为“帖撒罗尼迦策略”,就是“另有一个王”,这是他所倡导的,也是Stefan完全认可的方式。
使徒行传17章记录了在帖撒罗尼迦发生的事情。当时保罗已经在帖撒罗尼迦传了福音,也有人信仰并建立了教会,这引起了混乱。
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使徒行传17章6到7节)
第一批基督徒,当文化与信仰发生冲突,他们抵制了文化体系,把世界颠倒了。他们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仰,宣称耶稣是主。同时他们也侍奉身边的人,准备好承担造成动荡、颠覆世界的代价。Stefan认为这正是当代基督徒需要做的。他指出,基督徒需要训练自己抵抗违背我们信仰的文化制度,为我们宣称耶稣为主的权利而战。基督徒尊重他人宣称他们信仰的权利,也捍卫我们宣告信仰的权利。第一批基督徒还为信仰做了很好的辩护,保罗本着圣经与犹太会堂里的人辩论,说明耶稣就是基督(参使徒行传17章2到3节)。所以基督徒要将信仰宣告与结合当下实际为信仰辩护结合起来。
历史上教会有很多失败,比如奴隶制、种族主义、妇女权利和宗教自由,但是当我们查看圣经,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总是新约中,在第一代基督徒身上。所以,当我们与不公正的现象做斗争时,我们总可以回到新约,回到最初的基督徒身上,找到与这些不公正现象做斗争的动力。Stefan在此处回到开头提到的文化乱象,说有一位著名的瑞典基督徒领袖说,拒绝接受LGBTQI+是我们这一代教会犯的最严重的错误。Stefan反对这种说法,他说,在新约中,第一代基督徒在性的问题上采取了和周围文化不同的立场,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宣讲福音、建立教会、为信仰争辩以及爱身边的人之后,罗马帝国的性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传福音和为真理争论。
Stefan最后总结道,基督徒明确地希望为一个尊重多样性、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社会而战。我们希望保护每个人,没有人应该被仇恨、骚扰或压迫。但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上帝比我们特定的文化时刻更伟大,真理胜过潮流。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耶稣是主,我们的文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