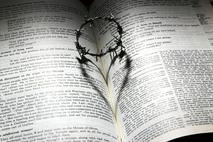引言:
华北神学院是一家在中国大陆消失多年的中国神学院。但是这家神学院曾在新中国建政之前(1949年),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神学院。在上个世纪新中国建政之前,中国有三所著名的神学院分别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金陵神学院,以及这所消亡于历史长河的华北神学院。也许现在很多人会对“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以及金陵神学院”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但是有很多人却对这所曾经大大影响中国教会的神学院一无所知。殊不知影响中国教会历史的“丁立美,贾玉铭,张学恭”等人曾任教于这所消失于历史长河的神学院中。1而这所神学院的创始人“赫士”曾为建立中国的保守派神学以及建造中国独立自主的教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如今大多数国内教内人士对他一无所知。
华北神学院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占据独特地位在于,赫士以及神学院带有强烈的基要主义色彩。而此色彩,正影响了该神学院的发展和办学理念,并因此培养了很多有力的工人。在同时期,1920年代,以王明道为代表的持基要主义的中国教会领袖也正在兴起。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教会主要是由宣教士建立并管理,而当时西方宣教士很多都受到了自由派神学院的影响,2甚至在30年代山东还要面临灵恩运动的冲击。而赫士以及华北神学院,自然不能在这场时代的洪流中置身于外。有趣的是,鼎鼎大名的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以及他们的校方也面临类似的冲击。3而二者都竭力的以保守派的神学立场回应当时的问题。华北神学院生逢乱世,到它撤离大陆的期间,不断受到社会动荡和神学动荡的冲击,而在这种动荡下,他们居然能够站稳立场培养工人,这是一项值得纪念的工作。
一、赫士与自由派神学分道扬镳
华北神学院的旧址是在今山东省的滕州市(滕州市在民国时期称之为滕县),而山东省曾经是美国长老会的重要传教基地。美北长老会于1861年进入山东省,在1861年至1899年分别在登州(1961年),烟台(1862年),济南(1872年),潍县(1882年),沂州(1891年),济宁(1892年),青岛(1899年)建立了传教地点。4在1882年11月一位名叫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的青年牧师,他曾师从改革宗神学家华菲德(B.B.Warfield),带着新婚妻子来到山东登州,开启了他漫长的在华宣教之旅。在来到山东登州之后,他曾与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一起在登州文会馆配搭侍奉,他在文会馆教授天文,地质,理财,数学长达18年,并于1896年接替狄考文担任监督并创办《山东时报》。5但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该学校受到了冲击,后迁往潍县,后改名为广文学堂,后来在此基础上于济南与神道学堂和医道学堂联合建立了著名的齐鲁大学。6该学院有三个院系,分别是文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同年,赫士担任齐鲁大学神学院的神学教授,后担任该校神学院代理院长一职。但是由于齐鲁大学是一所由美国的公理会、美以美会、美北长老会、美南长老会、信义会以及英国的浸礼会、长老会、循道会、行教会、伦敦会和加拿大的合一会共同组建的大学,7所以齐鲁大学神学院的很多教师也都是跨宗派背景,并受到了当时自由派神学的思潮影响,因此自由派神学思潮不断蔓延其中。8正如贝德士对当时各宗派的神学主张的观察:“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致力于合作与联盟,使他们放弃了加尔文传统的严谨,圣公会在坚定的教会架构下,容纳了许多新派思想和社会意识。” 9
与此同时,身为保守派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的赫士曾批评过其他宗派教员的自由派神学思想,他指出菲斯克(Fiske)曾在早晨礼拜时公开嘲笑旧约,将求雨祷告说成旧时代的迷信,他也指出某些教员嘲讽耶稣是童女怀孕所生的神迹,甚至否有耶稣的死里复活以及基督的神性。10所以对于保守派赫士而言,这种言论实乃难以接受的离经叛道之举。但是赫士的立场得到了长老会济南区会的决议支持11,另外赫士背后所属的教会以及同宗派神学生亦将赫士视为“全中国最好的神学教授”。
另外,由于中国教会难以接受英国浸礼会强化外国人对齐鲁大学的控制,并在1919年春,在没有中国人出席的外国教职员会议中提议要禁止不会英文的中国人参加教员会议,所以招致了中国人和长老会传教士的抗议。再加上该校对中国人参与管理的要求置若罔闻以及让该校的神学生感到并未给其创造理想的神学教育环境,所以导致很多神学生将赫士视为他们权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这使得赫士和支持他的教会与校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最终,赫士在1919年被迫辞职,因而导致长老会背景的神学生对该校失望,故而有18位神学生从该神学院退学,并一同聚集在山东潍县进行神学学习,他们邀请赫士为导师。12赫士也在《十年经过》一文中回顾这段往事:“华北神学院,创始于1919年秋,彼年因与齐鲁神科管理及道旨意见不同,长老会学员情愿退出,教员亦分离,同到潍县,另立神学”。13值得一提的是,在赫士离开齐鲁大学时,金陵神学院曾开特别会议欲邀请赫士担任该校教授,但因该校持开放的神学倾向的办学思路,所以赫士拒绝了这个邀请。这不难看出赫士是一位追求信仰纯正的保守派人士。
山东中国长老会为支援这群学生,于是纷纷退出了山东齐鲁大学神学院,并禁止向该校输送神学生,同时也在与长老会传教士着手创建新的神学院,1919年11月8日,济南区会召开决议宣布“长老会必须在山东建立尊重圣经的,自己的神学院。14同年12月4-5日在潍县召开临时董事会,确立该神学院名为山东神学院,赫士出任该院院长并任教,时年62岁。15另外美南长老会江北教区也被邀请一同建立该神学院。华北神学院的建校目的就是要抵制齐鲁大学神学院的自由派神学,所以在召开董事会时就确立了该校的建校宗旨就是:(1)教授上帝圣言所载的基督的基要教义,(2)着重以圣经为信仰与行为唯一且足够的准则,(3)保守有关神学,(4)圣经批评和讲经等方面的守旧教训,(5)传授基督教工作各方面的训练,(6)神学院主要由中国教会管理。 16
二、神学院南迁并成为北方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神学院
山东神学院刚建立时,办学情况举步维艰,教室是借用他人家中的地窖,校具均也是借用其他学校的破校具,但因着次年学校的运作步入了正轨,也有中国信徒的热心奉献,并于1920年3月再次召开董事会,要求美北长老会每年拨款,并争取到了南长老会以及中华基督教会的支援与合作。17随后,赫士与董事会考虑要为神学院建设新的永久校址。校方曾经考虑过迁往济南或上海,但又考虑到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基情绪,遂否定了这项提议。又因为江北教区的加入不得不另选他址,于是乎他们将眼光聚焦在与江苏北部接壤的鲁西南地区。值得一提的是,美北长老会济宁地区的传教士曾在滕县(在民国时期滕县隶属于济宁道)建立了深厚的教会事工,另外赫士也在滕县参与建立了当时的神学预科学校,即新民学校,再加上该地方是平沪铁炉的中点,又与江苏北部接壤。18所以赫士和神学院董事会将校址定为滕县,并于1922年9月正式迁到滕县,赫士及董事会的心志不局限于山东,而是希望建立中华北部的神学重镇,于是将神学院正式从山东神学院改名为华北神学院。 19
在该神学院草创时期,仅有18位神学生,1920年有24位神学生,但随着学校的南迁,1923-1924年学生人数,增长至84人。1925年学生就有120人而且这些学生是来自南北各省,甚至有新加坡、韩国等地的学生,并在1927年达至人数最高点即127人。仅从人数的角度考虑,该神学院已超过金陵神学院成为中国最大的神学院。
赫士对这所神学院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他坚定的拥护圣经是神的默示,高举圣经无误的权威,以及保守派的神学思想,他曾说“华北神学院永远不培养贬低基督,怀疑福音的人。”20在当时中国有许多跨宗派的神学院,但赫士将华北神学院塑造了一间保守主义,追求纯正信仰的改革宗背景的独立神学院,可以说他成功地与其他受自由派影响的神学院分道扬镳。该学校也重视对学员关于圣经语言,音乐,宗教比教学,旧约考古学,圣经地理,基督教社会学等方面的培训,为中国近现代教会培育了大量的信仰纯正,受到正规神学训练的传道人。另外,神学院也聘请了许多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毕业生,但是该校仍遭遇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也许是因为该校强调基要主义的立场才导致师资不足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凡是担任该校的董事和教员就必须认信该校的信条,该信条大致讲的是:(1)相信圣经66卷均为神的默示(2)认信三一神(3)基督由童女所生并从死里复活并再要降临(4)基督为信徒赎罪(5)基督的复活是信徒复活的确据(6)信徒蒙拣选,重生,成圣皆为圣灵之工(7)魔鬼必最终受审判(8)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由圣灵重生并由真基督徒组合而成。21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秋著名的基要派领袖贾玉铭受到了赫士的邀请,成为了华北神学院的教员,但在1929年贾离开了华北神学院,很多人认为贾与赫的分道扬镳是因为他们的千禧年观的立场不同而导致贾的出走。但是《以信废用》的作者认为,贾是因为受邀作金陵女子神学院校长一职,要维护人际关系的原因,最终离开了华北神学院,而不是神学上的分歧导致的分离。 22
三、赫士与灵恩运动的分道扬镳
在1927年一直到30年代,山东地区产生了教会的属灵复兴,史称“山东大复兴”,而山东复兴分为“西方式”和“本色化”的两个复兴中心。西方式的复兴是从沿海城市烟台开始的,这场复兴是由西方传教士主导发起的,而本色化复兴则是从费县的开始的,这场复兴运动逐步形成了“灵恩运动”。另外随着一些著名的传道人来山东传道,“灵恩运动”慢慢地向周边地区扩散,有意思的是,基要派大本营华北神学院所在的鲁西南地区也因此经历一场灵恩运动,甚至泰安以及周边等地后期也发起耶稣家庭的“灵恩运动”。231931-1935年宋尚节多次来到济南,泰安以及与泰安接壤的济宁传道,宋的到来无疑是为这场复兴运动添了一把火,而这把火焰也顺势烧到了滕县。24当灵恩的火在山东被点燃时,随之出现了“寻求方言,异象,昏厥,预言,神医,赶鬼等灵恩迹象”,这场运动也展现出了本土色彩,甚至是表现出了当地民间宗教色彩。 25
这场运动给保守派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于是各地保守教会禁止会众加入灵恩运动,不准以“洗脚”代替洗礼,以“灵餐”代替圣餐,也不准强迫他人认罪,与死人交往以及接受神医等活动。26当赫士面对这场灵恩运动时,也是持负面的态度,他说道:“灵恩运动似乎是魔鬼用以维护其统治的一个办法。一个有着良好开端,预示着良好结果的运动有时会被他利用,结果只会带来伤害。”赫士还说:“除了彻底了解基督和使徒所教导的真理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防止别人散布错误的思想。”27当华北神学院表态拒绝灵恩运动时,该神学院的著名教员丁立美则向该院提出了辞职,并且引发了该院神学生对赫士是否重生得救的质疑。28似乎为了抵制灵恩运动,该校在1933年7月组织各地的信仰纯正的青年学生,来一同学习,好让信徒对外传扬福音,对内能够持守真道。29于是在校方的努力下,这把火终于在此被扑灭。
四、赫士之死与华北神学院的来生
在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使得中国教会以及西方传教士不得不面临更大的挑战,而这场挑战要持续到1945年才能结束。在1937年-1941年12月6日前,因着西方各国尚未对日本宣战,西方传教士还能服侍中国的信徒,亦或者可以返国或逃难。30但随着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部分的在华西方传教士正面临着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的命运。1938年日军占领了滕县,而身为美藉宣教士的赫士以及华北神学院的美藉传教士均放弃了返回美国的机会留在了滕县,并在1943年日军逮捕了华北神学院的全体美藉传教士,统一送往潍坊集中营关押,并在1944年秋,赫士和中国教会史上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李爱锐一样(Eric Henry Liddell)死于潍县集中营。31讽刺的是,潍县是赫士正式创立华北神学院的地方,但最终也是他结束一生服侍的地方,他最主要的侍奉工作始于潍县,而终于潍县。
华北神学院的滕县校址于1945年遭受日军的毁坏,随即临时迁往徐州,但随着侵华战争的结束,国共内战的爆发,1948年底,徐州是淮海大战的主要战场,以避免战事遂在1949年迁至无锡,但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1949年华北神学院在中国大陆的校务完全终结。49年之后,有一批华北神学院毕业生前往了台湾,直到1991年在胡鸿文等人的领导下,华北神学院正式在台北复校,所以该神学院正在以另一种形式活跃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32
结论
《平信徒海外传教调查报告》评价赫士说:“赫士博士是中国迄今为止基要派神学最有力的阐发者。他与普林斯顿的帕顿(Patton)院长和梅钦(Machen)博士同属一个教义流派,并且为中国的保守派教会作着那些美国学者在美国作的同样的事情。”33可以说赫士为中国教会培养了一大批的中流砥柱。纵观赫士的一生,他所做的最终要的工作就是竭力的持守保守派信仰,并为中国教会建立基要派的神学阵营,与自由派和灵恩派思想分道扬镳。笔者研究赫士与华北神学院的目的就是要从历史神学的角度去思考“中国当下的教会,该如何抵挡教会所面临的“祛魅化”“世俗化”,以及教会如何选择路线的问题”。从赫士的一生不难发现,他是生于乱世的传教士,他经历过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但他的一生精力不是逃避乱世,而是在持守真道,甚至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都在竭力地持守他所信的真道,在日军的迫害下仍然在集中营中站稳立场。这是后世的中国教会的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在上帝[沉默不语]的时代,你我是否有勇气站稳立场,持守真道?在后疫情时代,在世界各地不断燃起战争硝烟的世代,教会内部需要兴起工人来勇守真道,奋力传扬古旧的福音。
今天我们要面对世俗化的思潮,现代年轻人被人称之为Z世代(成长于智能手机的一代人)。对于现代人而言,信仰变得没那么重要,反而手机的资讯、社交媒体、如何达到事业成功更为重要。这是充满焦虑的世代,因此从历史的借鉴意义来看,教会需要兴起工人成为逆行者,要教导来自于圣经的世界观捍卫立场。当代教会危机就是没有成为抵挡违背圣经价值观的中流砥柱,反而被牵着鼻子走。后人不忘前人之师,在后疫情时代,在世界各地不断燃起战争硝烟的世代,教会内部需要兴起工人来勇守真道,奋力传扬古旧的福音。华北神学院在中国大陆的时间不算特别长,仅有三十年,但却完成了神交托的使命。笔者认为,在当下神需要的是坚守真道,敢于服侍的人。
脚注
2023年10月2日晚七点电话采访上海尹牧师。
姚西伊,《为真道争辩》,(香港:宣道出版社,2008),140页。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watson-hayes
狄德满,《华北的暴力和恐慌》,崔华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60页。
相关论述见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watson-hayes
肖会平,《合作与共进》,(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45页。
同上。
文章:郭建福,《赫士: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第4页。
贝德士,《贝德士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择》,章开沅、马敏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229。
姚西伊,《为真道争辩》,(香港:宣道出版社,2008),139页。
赵曰北,《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30页。
华北神学院百年校庆宣传片见https://youtu.be/0vB7R5XTsCk?si=gQXByJzyrGJGAT6S
《华北神学院年刊》,南京灵光报社,1930年,第1页。
姚西伊,《为真道争辩》,142页。
郭建福,《赫士: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第5页。
赵曰北,《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36页。
姚西伊,《为真道争辩》,142页。
赵曰北,《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70页。
王德龙,《以信废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94页。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watson-hayes
华北神学院简章,上海档案馆全宗档U110-0-39,上海市档案馆。
王德龙,《以信废用》,104页。
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6页。
宋于1931年5月,1934年3月,1935年春和1936年3月多次来到滕县。
连曦,《浴火得救》,何开松、雷阿勇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76-81页。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371页。
姚西伊,《为真道争辩》,175页。
连曦,《浴火得救》,80页。
赵曰北,《历史光影中的华北神学院》,99页。
裴士丹,《新编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尹文涓,(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9),190页。
华北神学院(台湾)https://www.nctstw.org/華北簡介/
同上。
http://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watson-ha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