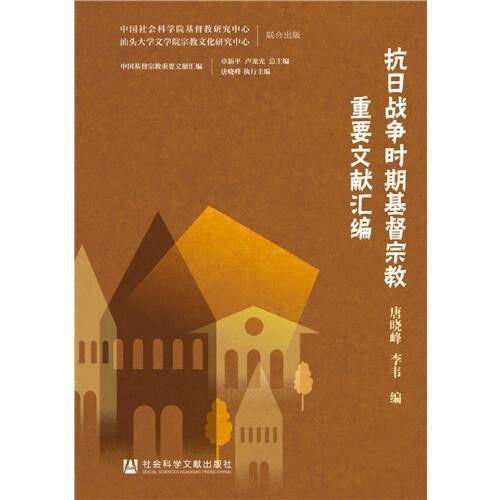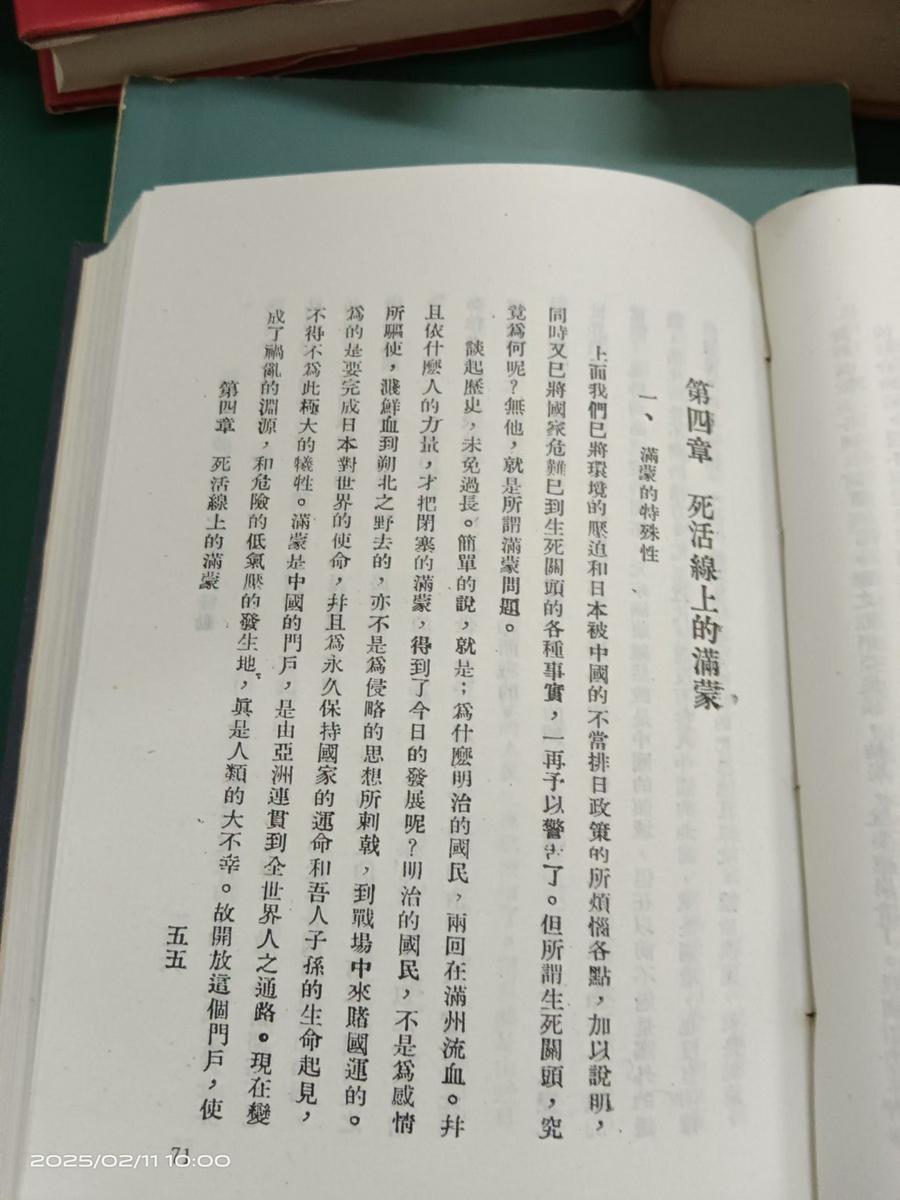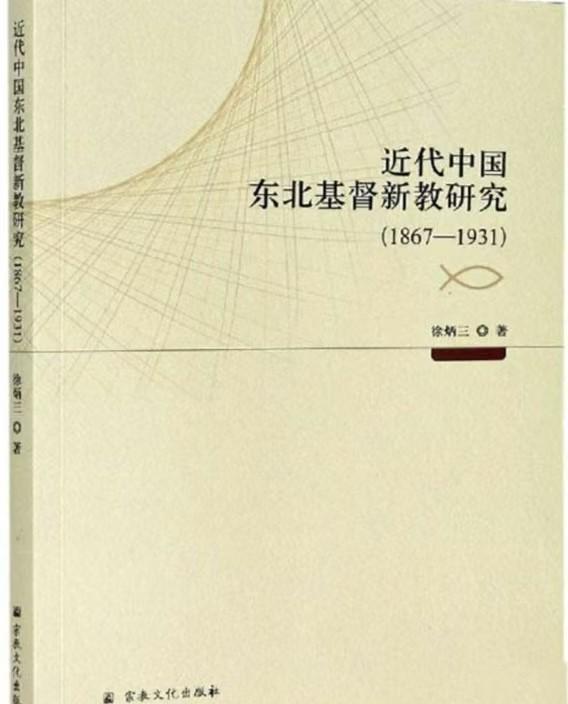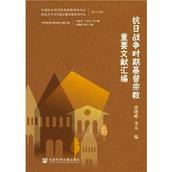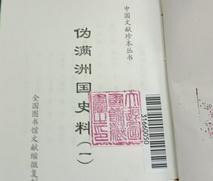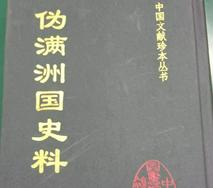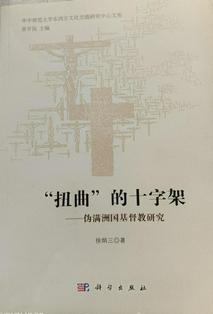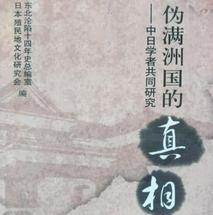问候亲爱的各位在基督里平安!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
在外部近代化浪潮中,东北地区一直处于日俄争夺胶着中,最为令人气愤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日俄两国的战争居然发生在第三国,即我们中国的东北辽宁。到后来殖民瓜分,其中经历清朝封禁 、大移民、张氏父子统治以及伪满洲时期 ,社会变革剧烈 ,阶层反动汹涌澎湃 ,这在根本决定了东北区域的近代化进程发展不一般 。在内部社会变革和外部时代转轨形式的冲击下,基督教作为集先进和落后于一身的外来宗教,在东北地区传播和发展波澜起伏 ,同样经受了日伪时期的强烈冲击。而大多数东北的基督教信徒、教会是爱国爱教的,也是与东北人民一起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
七、东北基督教界对日寇侵华战争和迫害的不屈不挠的抗争。
日本教会能够迅速掌控东北新教,也有西方教派自身的原因。西方传教士与日本教会的关系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张,在日寇的武力淫威胁迫下,他们总是尽力与日本教会保持良好关系。东北传教士曾多次应邀访日,东北的教会人士经常参加日本人的集会,与日本牧师联合祈祷。“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组建的过程中也多有西方传教士参与的身影。“七七”卢沟桥战争后, 处于危境的东北教会在日本教会中寻求靠山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从日本请来牧师小仓,由他出面与日伪政府交涉,避免了“满洲基督教会本部”的直接控制。哈尔滨西门脸教会分别拉来山下水幸和石川四郎做顾问,东北长老会“为应付现实”也把石川拉拢进来,这样,“经彼多方奔走,教会产业始得保守,未被没收”。随着日伪基督教政策的不断紧缩,西方教会的自由空间日益缩小,忍让和谨慎原则往往不能发挥效力,在基督教根本原则遭到践踏时,传教士也会进行有限度的抗争。1935年伪满洲国对传教人士和基督徒大逮捕事件发生后,传教士为营救被捕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请山下水幸等日本牧师出面讲情,并亲自造访日本官员和英日领事、致信日本最高官员,传教士方德立还试图通过法律渠道为被捕者辩护。(参阅徐丙三:《伪满体制下宗教团体的处境与应对》第57页)
“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的时间内,是20世纪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期。“九·一八”之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对上海发起了军事进攻,十九路军奋勇抵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斗志。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略军的疯狂残杀,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伤害,全国军民的前赴后继。英勇奋战,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广大中国基督徒和爱国教会领袖,纷纷与爱国同胞一起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基督教两会编:《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
其实,在日寇侵略东北时期,东北基督教界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东北基督教信徒、教会在面对日本侵略时的复杂态度和思想分歧。
日本悍然侵占中国东北,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中国基督教界表现出高涨的救国热情。在“九一八”战争爆发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分别收到香港、广东、北平、保定、锦县、苏州基督教教会联会、上海传道联合会、厦门基督教任职会、山东临清公理会、湖州监理会、南京金陵神学院、南京妇女节制会、哈尔滨中华基督教会、上海美华浸会书局全体及张之江、范定九等单位和个人的函电,要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出救国呼声。为了响应全国教会的呼吁,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在1931年9月28日的常务会议上,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名义分别致电国际联盟、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日本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致全国教会书,表达中国教会对日本侵华的主张。并发表了《为日军侵占东省事敬告全国教会书》,谴责了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东三省的行为,指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也对国际联盟所倡导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联盟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持公道,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纠纷。(详见《真光》1931年第11号,第99页。)
具体来说当时在中国和东北基督教界对于抗日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即反战言论(主和派)和主战言论(主战派)之争。反战言论认为所有战争都不符合道义,都应该遭到批判,因为任何战争都会毁灭物质、摧残人性,给人类带来灾难。个别基督徒甚至极端地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根源,“并不在野心的日本,又不在软弱的中国,乃是世界各国所信仰的所依靠的武力主义;就是以武力为实行一个国家政策的工具”。
主战言论则坚称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它强调日本的暴行是全人类的罪恶,基督徒参加抗战并非只是为国尽忠,更重要的是要铲除罪恶、维护正义。“此次日本的暴行,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国民,出为反对,就是世界任何国民凡属基督徒,均应反对,因为他们的暴行,是世界人类的极大罪恶。”退一步讲,即便仅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日本侵略,与基督教教义也不冲突,“因为此次日本出兵东三省,不但破坏国际公法,并视人道正义为无物!所以我们无论从国民的立场或信仰的立场,皆当奋斗”。主战言论并不否认战争的残酷性,但认为不进行正当防卫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有时为了救人的缘故,不惜出于自卫目的的战争,日本以强暴的手段占领东北三省,欺骗、诱惑、恐吓、种种卑鄙无赖的行为,没有道理可以同他讲。”
主战派的基督教徒主张积极抵抗日本的侵略,认为抵抗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基督教的“爱敌”原则不应被理解为对侵略者的纵容,而是要在抵抗中体现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例如,一些基督教团体在“九一八”战争后逐渐认识到抗战的重要性,开始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如救济难民、救护伤兵等。此外,部分教会领袖也呼吁基督徒参与到抗战中,认为这是基督徒的本分。
主和派则倾向于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他们强调基督教的和平与爱敌原则,认为应避免直接的武力对抗。他们主张通过祈祷、和平谈判等方式来缓解紧张局势,认为这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解决方式。然而,这种观点在当时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亡国奴心理”,遭到了主战派的强烈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九一八”战争后,伪满洲国对基督教的迫害,东北基督教界的主流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初,部分基督教徒持非武力抵抗或“救国先救人”的思想,但随着战争的残酷现实和日本侵略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徒开始认识到,只有坚决抵抗才能救亡图存。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了基督教徒在民族危机面前的觉醒和责任感。
在日寇侵略东北时期,东北基督教界内部的主战派和主和派观点反映了基督教徒在面对侵略时的不同思想和态度。尽管存在分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界逐渐认识到抗战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中国信徒的态度与西方传教士相似,在日寇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在没有任何羽翼庇护的情况下,若想生存只靠沉默和退让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沦陷区多数人民的无奈。但中国基督教信徒毕竟是炎黄子孙,民族主义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常常有所展现。如日本人企图建立“中国牧师联合委员会”的号召因遭抵制而流产;有的日本基督徒欲向一个教会组织提供帮助,连提10次均遭拒绝;中国信徒偶尔也会对抗政府,如吉林延边敦化在庆祝“满洲国庆日”之际发出特别通知书,但基督教没有参加;吉林青年会在溥仪视察教会时拒绝临时检查;在教会小册子上常有“国耻纪念日”、“不承认日满”、“我等中国人”等词句;教会学校师生常有反日不敬的言行;日伪协和会强迫基督教各派入会的努力也宣告破产。这些大都是自发的零星行为,但亦反映出中国信徒与西方传教士的差异。
日本教会配合日伪政府控制东北基督教,其动机很复杂。日本教会与政界联系密切,部分日本信徒还有政治背景,具有配合日本侵略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思维确定无疑。日本基督徒首先是日本国民,在多数日本民众为军国主义思想欺骗而掀起民族主义狂潮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思想亦不足为奇。战争期间日本基督教界的主流对日本侵略扩张政策是支持的,在“九一八”和“七七”前后,日本基督教界都曾发表支持日本政府的宣言,并在实际行动上对侵略活动大力协助。另一方面,很多日本信徒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不自觉地为日本政府利用,成为侵略者的帮凶。如日本长老会长老武藤富男,坚持认为“满洲国”就是协和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信仰、精神和道德符号等。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伪满洲国时期,东北基督教徒,包括外籍传道人,在日伪政权的高压统治下,通过多种方式展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比如:
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削弱学校中的教会势力之后,又推出了“惟神之道”,将国家神道提升为国家信仰。1940年,在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皇宫修建了供奉代表天照大神神器的“建国神庙”。“奉安”当日,关东军指令溥仪发布《国本奠定诏书》,称“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此后伪满政府颁布《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祭祀令》,要求各地建造“建国神庙”,到1942年全东北的“建国神庙”已达240所。同年12月8日,又颁布《国民训》,强调“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将崇敬天照大神作为一种“国民”义务。要求教会学校的学生们参加日本神道教的祭祀及供奉天照大神,这在教会内引发了巨大的骚动。一些教会成员认为,必须拒绝本势力的无理要求,宁可立即关闭所有学校;另一些人则认为,有关推行神道教的法令与其说是宗教法,不如说是出于政治考虑,他们寄望于向日伪政府妥协,以便维持教会对学校的控制,他们援引日本基督徒和牧师的说法,参加神道教仪式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没有冲突,如同英国人起立唱英国国歌一样。传教士会议在辩论之后进行投票,以100票对4票的结果决定抵制日伪政府的要求。绝大多数人认为神道教与基督教之间存在信仰冲突。
在日本殖民当局的种种压迫下,1939年10月,各教会无奈决定关学校。日伪政府买下了爱尔兰长老会在营口、吉林、广宁、新民和榆树5所教会学校,以及苏格兰长老会的3所教会学校。苏格兰长老会总会1940年说,很遗憾地收到了东北两处教会关闭的消息,他们认为有必出于道义理由放弃在东北的教育工作。总会对于东北传教士遭到日本殖民政权强制剥夺传播福音权利的境遇以及东北长老会遭受的损失表达了情。这标志着传教士们在东北地区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事业在日本殖民权的宗教统制下终结了。(伪满洲帝国教育会编《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上),1938,第490页。)
在日伪政权试图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拉拢东北基督教徒时,中国信徒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例如:
1.拒绝救济与捐助。
日本曾试图利用中国兵工厂生产的饼干救济灾民,但这一行动并未得到中国教会的响应。此外,日本教会曾提出给中国牧师400元捐助,但中国牧师坚决拒绝。这种拒绝不仅体现了基督教徒对信仰的坚守、圣洁,也反映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抵制。
2.抵制“中国牧师联合委员会”。
日本试图建立“中国牧师联合委员会”,从组织上完全控制中国的基督教。但这一号召因遭到东北基督教徒的抵制而流产。这表明在日伪政权的压迫下,东北基督教徒仍然保持着对日本侵略者的警惕和抵制。
3.秘密传播信仰。
在日伪政权的严密监控下,东北基督教徒通过秘密方式传播信仰,以维护基督教的纯洁性和独立性。他们常常在家中或秘密场所举行小型聚会和家庭礼拜。这些活动通常在夜间或隐蔽的地点进行,以避免被日伪政权的特务和警察发现。信徒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组织活动,彼此之间保持高度的警惕和信任:这种秘密传播不仅体现了基督教徒对信仰的忠诚,也反映了他们在艰难环境下的坚持和勇气。
4.销毁“危险”书籍。
为了避免被日伪特务发现,一些基督徒秘密销毁了带有来自于上海印记的书籍。这一行为反映了基督教徒在极端环境下的谨慎和对信仰的保护。
5.抵制日伪的组织控制。
日本试图通过建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等组织来控制东北基督教,但遭到教会的抵制。例如,1941年日本牧师石川四郎试图将东北基督教各派合并,但遭到教会内部的强烈反对。
6.维护教会独立性。
面对日伪政权的干涉,东北教会努力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如哈尔滨的美国传教士曾集体致函伪民生部大臣,反对《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指出该法令破坏了信仰自由。
7.反对参拜神社和祭孔。
日伪政权强迫教会学校祭孔和参拜神社,这违背了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戒律和原则。东北长老会曾明确拒绝参加祭孔活动,并表示“将对福音的真理作明确的、不妥协的见证,对上帝保持不动摇的忠诚”。
8.抵制教育权的收回。
1939—1940年,日伪以收回教育权为借口,通过强买校产的方式没收教会中学数所,小学也大部分停办或被没收。教会方面拒不妥协,但在日寇武力的淫威下最终于1939年放弃了除医学院和神学院外的学校。
9.坚持传播基督教真理。
尽管日伪政权对基督教文字事业进行了严格限制,但一些教会刊物仍然坚持传播基督教真理。例如,圣经公会传教士罗培生(J. H. F. Robertson)在沈阳秘密进口上海印刷的圣经单张并装订,以满足信徒的需求。
10.牧师和教会人士的反抗。
公开反抗与被捕:一些牧师和教会人士因公开反抗日伪政权而被捕。例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1935年秋,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为名,先后逮捕了46名基督徒,大都为教会的上层人士。其中,基督徒张尚民和牛光仆各被判处20年徒刑,牧师刘国华、女学生刘爱光等人被长期拘禁和严刑拷打。
11.坚持信仰与见证。
在日伪的迫害下,许多牧师和教会人士,包括欧美的传道人,仍然坚持信仰,为基督教的真理作见证。
(1)在我的家乡辽宁省鞍山市的岫岩县,有一位传教士中文名字叫做宁乃胜(1875—1945),原籍是丹麦人,曾在美国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加入美国籍,医疗传教士。1875年6月29日出生在丹麦霍斯艾厄,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通过医学考试。跟随他一起来到中国的宁乃胜夫人,护士、美国人,生于1873年1月3日。1907—1940年间随同丈夫来到岫岩,在丹国医院任护士。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抗日武装中国少年铁血军领导人认为,宁乃胜已加入美国国籍,如果将他绑架可以导致美国对日军施加压力造成国际纠纷。4月11日由抗日武装中的刘天福装扮成病人,乘宁乃胜出诊之机将他绑架带走,铁血军提出交换条件,遭到日方拒绝。铁血军见扣押他对日方已构不成威慑力,10月25日由队长于同治将宁乃胜安然送回医院。
宁乃胜在铁血军中滞留6个多月,他跟抗日部队随军期间,曾多次尽心尽力医治、抢救伤病员,他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与抗日队伍结下了友谊。宁乃胜回医院后派护士苑松廷代表本人携带1万元钱、一箱药品,交给铁血军总部。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宁乃胜转到黑龙江省绥化医院,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他退休回美国,也有说他1940年离开中国,1945年4月11日去世,时年70岁。
(2)还有辽宁沈阳神学院院长、外籍牧师方德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逮捕关押三个月,但他始终坚守信仰。
沈阳神学院(原奉天神学院),即现在的东北神学院前身,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基督教神学院,由英国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罗约翰牧师于1894年创办。1934年至1949年,方德利(Foster)担任院长。在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基督教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和控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同化和压制当地宗教团体。他在此期间培养了许多基督教传教牧师、教师和教士,为东北地区的基督教教育和传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好,谢谢您的阅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继续关注。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