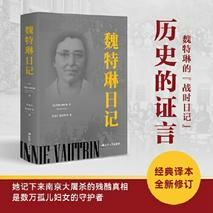英文God应该汉译为上帝还是神?这个圣号问题的争论早在1840年就出现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争论是在基督新教内。
在委办本翻译过程中,圣号问题(Term Question)最具争议性,涉及圣号(希伯来文音译“Elohim”与希腊文音译“Theos”)如何翻译的问题。1840年代委办本的焦点,主要是考虑应以“上帝”或“神”字翻译圣号。大体上赞成以“上帝”翻译圣号者,是试图从中国传统的经学典籍和祭天仪式,论证“上帝”在中国人的信仰中是超越独一的,因此这是一个绝对称谓,而非专有名称。麦都思是赞成“上帝”的委办本译经者,而其他传教士也有类似的见解,例如理雅各。至于赞成以“神”翻译圣号者,尤其见于文惠廉的论文。文惠廉认为,中国宗教是泛神论的,“上帝”只是众神之首的名字,正如昔日译经者没有用宙斯(Zeus)或朱比特(Jupiter)等语翻译“Elohim”,故此也不可以用“上帝”来翻译,反而“神”才是指称“最高级的存有者”的属名。
在汉语圣经翻译中,对于“God”一词的翻译存在的争议,甚至因此影响到圣经中文版本的汉译一度暂停。主要围绕着神与上帝这两个译名展开。当然,无神论者还把God翻译为“天”,比如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把“My God”翻译为“我的天”。我们主内关于God是神还是上帝这一争议反映了不同教派、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解与选择,不过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在中国基督新教中早已没有了这种争议。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题目主要目的一是对God汉译的历史有个了解;二是有助于我们対信仰的深入了解;三是也许有助于传福音;四是也表面笔者的观点。
一、基督教不同教派对God的汉译
1.天主教的翻译:在唐朝时期,景教传入中国时,传教士曾借用道教、佛教中的词汇来表示“God”,如“天尊”、“佛”等。到了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一度使用“陡斯”作为“God”的音译。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后来采用了“天”和“上帝”来翻译拉丁文“Deus”,但因理解上的差异,最终选择了“天主”和“上帝”。然而,这一选择受到了其他传教士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两个词不能准确表达“God”的含义。1704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下令,天主教官方使用“天主”作为“God”的译名。
2.新教的翻译: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抵达中国,他选择了“神”作为“God”的翻译,而没有采用天主教的“天主”。他认为“天主”一词不被中国人所接受。然而,新教传教士中也有支持“上帝”译名的,如马礼逊的助手米怜。他认为“神”可能会使中国人误解“God”只是众多神明中的一个,而“上帝”更接近“God”的意思。这一争议在19世纪的传教士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形成了“神”派和“上帝”派两个阵营。
“神”派观点:这一派认为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最高存在,所以只能选择一个中国众多神明通用的名词来代指。他们认为“神”一词正是中国语言中各神明通用的名称,尽管中国人使用“神”一词时,所想到的不一定是“God”,但这一译名已经是最接近“God”含义的词语了。
“上帝”派观点:以理雅各为首的英国传教士支持“上帝”译名,并有针对性地批判美国传教士所提到的中国人的信仰和“类名”问题。他们认为,在中国存在一个最高存在“上帝”或“帝”,万物因它而成,受它管辖,而这个受中国人所崇拜的最高存在“上帝”或“帝”即西方人所崇拜的“God”。
这场争议不仅涉及语言转换问题,还涉及到中国人的宗教文化和基督教哲学层面。最终,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导致了不同版本的《圣经》汉译本中“God”的译名出现了“神”和“上帝”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场争议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概念移植的困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的国家中。
二、新教早期的译名争论
1807年9月8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几经辗转和数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到达中国的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掀开了新教来华传教史的第一页。马礼逊到达广州后隐匿在美国商馆中,非法居留下来,并开始学习汉语。1808年他按照伦敦会的指示开始翻译圣经,1813年完成了《新约全书》,1814年开始翻译《旧约》。其间另一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也加入这项工作,1819年11月25日译完全部《旧约》,1823年装订成21卷在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而在马礼逊译本出版之前的1822年,浸信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Marshman)和助手拉撒(John Lassar)在赛兰坡已经完成另一个中文圣经译本。这两个译本都参考了同一个译本,就是大英博物馆藏的天主教传教士巴设(Jean Basset)的译稿,二者都采用了“神”这个中文词来翻译“God”。但马礼逊本人并不固执于“God”的唯一译名,他的著述中也用“真神”、“真活神”、“神主”、“神天”、“主”、“上主”、“上天”和“天地之大主”等来指“God”。
关于“God”的翻译,马礼逊曾经表示:“最佳的方法是让这个字(‘神’)继续被采用,直到教士可以找到另一个基督徒广泛接受的固定用法为止,正如在基督教神学中,‘Theos’一词是希腊语,在英语中意为“上帝”。拉丁文的‘Deus’……一样。”他的助手米怜则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反对“神”一词,改用“上帝”。马礼逊译本虽超越马士曼的译本,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但这并不能长久掩盖译本本身的缺陷,其中“God”译名的不统一也成为遭人诟病的缺陷之一,致使传教士中修订或重译圣经的呼声越来越高。实际上,马礼逊自己对他的译本也并不满意,但生前过于繁忙,没能实现修订之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子马儒翰(John Morrison)。1835年,马儒翰和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向“英国与海外圣经会”递交了一份修订计划,提出要修订出一个比马礼逊译本“更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圣经译本。同年,麦都思、马儒翰、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也译为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和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等四人组成一个修订小组,由麦都思主持,年底就完成了一个新的《新约》译本。1836年,他们开始在新加坡分批刻印此译本。次年又在巴达维亚出版合订本,名为《新遗诏圣书》。1836年,上述四人又着手修订《旧约》译本。1838年,由郭士立主持的《旧约》修订、出版工作完成,名为《旧遗诏圣书》,主要用“上帝”翻译“God”。这个译本后来被太平天国采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在传教士中,它像马礼逊译本一样存在争议。传教士们认为无论是新译本还是旧译本都不太符合汉语语言习惯。于是,一种不断增长的、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有的、追求更好译本的强烈愿望就出现了。这样,传教士决定召开会议,解决圣经翻译的相关问题。
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以麦都思为首的伦敦会传教士召集来华新教传教士到香港开会,讨论联合重译圣经之事。参加者包括伦敦传道会的台约尔(S.Dyer)、合信(B.Hobson)、理雅各(James Legge)、麦都思、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亚历山大施敦力(A.Stronach)、约输施敦力(J.Stronach);美国公理会的裨治文,美国浸信会的怜为仁(D.B.W.Dean)和罗孝全(I.J.Robert);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的勃朗(S.R.Brown);主席为麦都思。这次会议的目标是翻译一个新的具有权威性的通行译本,以取代旧有的圣经版本,由于传教士历来对“Baptism”(洗礼)、“deity”(三位一体的神性)、“Scripture”(圣经)三个核心用词译法不一,会议决议成立三个小组分别加以研究和讨论。结果其他两个词的翻译都达成一致,由麦都思和理雅各主持的“deity”一词的讨论却产生了更大的分歧。麦都思极力主张用“上帝”,理雅各则坚持用“神”,彼此相持不下。由于问题涉及传教士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理解,而就当时传教士所能达到的认识程度而言,都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来作出决断,与会者决定将问题留待日后由是次会议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审议。此后,许多传教士便开始致力于“God”翻译问题的研究,部分传教士则撰文在《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上讨论,支持“神”与支持“上帝”的双方针锋相对,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试图说服对方。其中“神”派代表人物是裨治文、娄理华(Walter M.Lowrie);“上帝”派代表人物为麦都思、郭士立。到1847年第二次译经会议召开,更多的传教士加入了争论,将讨论推向高峰。
第二次译经会议于1847年6月22日在麦都思上海的家中举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议的重任实际上落在麦都思、文惠廉、约翰施敦力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身上,尤其是麦都思和文惠廉负担更多。会议期间,再次遭遇“God”的翻译问题。委员们大抵一致同意没有任何一个中文用词可以准确表达“God”的意思,但在哪一个译名较为合适的问题,最后分裂成两派:麦都思、约翰施敦力等为“上帝”派,文惠廉、裨治文、娄理华、克陛存等为“神”派。双方运用各自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中文的知识进行讨论,并将讨论延伸到对神学和中国几千年文化和宗教的理解方面去。修订圣经的工作因此从7月5日延至11月22日,委员会希望各个委员能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集中处理相关的争论,求得最后的解决。在这四个月里,两派传教士不仅全面考虑“Elohim”、“Theos”、“god”、“gods”、“God”、“神”、“帝”、“上帝”、“天”、“天帝”、“天主”等概念和词语的意义,还旁及“灵”与“spirit”的翻译,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及至11月22日,讨论并未得到协调,于是决定投票解决。有意思的是投票的四个人中,“上帝”和“神”二词各有两人赞成,不分高下。委员会无力解决这个难题,就将它推给英国和美国圣经公会,由他们来决定。在等待两家圣经公会的决定期间,部分传教士又提出其他解决办法。希望能打破僵局,比如,音译的方法,另选其他用词,将“God”和“gods”分开用不同的词翻译,或者用“神”一词,而在译本卷首加上解释说明等。但这些方法均未得到中央委员会和两家圣经公会的采纳。最后,两家圣经公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英国圣经公会主张用“上帝”,美国圣经公会则赞成用“神”。为了避免分裂,也为了不影响出版进度,天主教版的圣经和基督教书籍中用“上主”翻译“God”。因为最近出版的白汉理和包约翰的《新约》译本以及其他的书籍都在用这个译名。杜步西还提出了“Spirit”翻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当前传教士一派用“神”翻译“God”;另一派用“神”翻译“Spirit”,造成了中国教会思想的混乱,传教士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三、关于God的继续讨论
这里,我们首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教务杂志》:《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是由在华西方宣教士于1867年至1941年间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这份杂志不仅记录了在华传教士的传教工作、语言学习及生活心得,还详细记述了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译介和评述。由于它所记录的年代恰逢中国政治社会巨变的转折期,因此《教务杂志》成为了非常珍贵的历史研究素材。
《教务杂志》曾经刊出一篇题为“给大会的一个建议”的文章,提出传教士大会应该注意着力解决的问题,其中第一个建议就是关于“God”译名统一的问题。作者谈道,当前有五种常用的词:“天主”、“上帝”、“神”、“真神”、“老天爷”。分析这几种用法,各有利弊。作者称自己可以接受大会确定的任何译名,关键是要统一,因为译名的不同使中国人本来就不清晰的God观念更加迷惑不清。还有,一封通信中列举出目前有利于解决译名问题的五种理由,认为当前正是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总体来看,传教士大会前《教务杂志》上出现的关注译名问题的信息不多,且比较温和。
1894年11月《教务杂志》上公布的一份译名问题的调查结果,使天平开始倾斜。这是由《教务杂志》的编辑进行的一次调查。调查共发出函件600份,范围是中国各地的传教士,内容是要求回答他们所用来表示God和Holy Spirit的中文词。最后收回函件351份,来自中国各地,非常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如下:
God的汉译:
173人赞同为上帝;65人赞同为神;36人赞同为天主;42 人赞同为上帝和神;8人赞同为神和天主;6人赞同为上帝和天主;3人赞同为上主;22人全部赞同。
Holy Spirit汉译:
179人赞同为圣灵;147人赞同为圣神;25人赞同为圣灵和圣神。
这次调查结果第一次以较为全面的统计数字显示出当时译名运用的总体情况,对传教士把握译名问题解决的方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传教士指出,这些数据已经明确显示出译名妥协的方向,那就是用“上帝”来翻译“God”。1901年12月,《教务杂志》的编辑者再次援引这一统计结果,呼吁传教士遵从潮流,用“上帝”和“神”译“God”,用“圣灵”译“Holy Spirit”。
1904年1月,高葆真总结道,译名争论过去数十年了,现在,除了零星的反对声音外,“上帝”一词已广为接受,绝大部分出版公会也已将之作为唯一的译名,其他出版公会则把它作为一个为许多传教士读者所需要的译名。他还提供了新教团体1892年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各译名所占的百分比:“上帝”,91.38%;“神”,5.44%; “天主”,3.05%;“上主”,0.13% 。这些数据与1894年的调查数据互相印证,显示出“上帝”一词所占的绝对优势。
在1890年5月的传教士大会上,译名问题并没有成为传教士关注的焦点。虽然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大会还是赞同要有合一的圣经(除苏格兰圣经公会外),在译名和语体这两个过去争论比较大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致意见。从会议决议中看到,关于译名,决议同意各圣经公会可以根到翻译的限度,即无法靠翻译一次性地正确传达圣经观念。
四、最终的结果和笔者的观点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和实际传教工作的经验,传教士对语言和翻译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意识到在语言和翻译无法满足忠实于原文这一原则的情况下,解释是一个有效的弥补途径,这种解释既可以通过传教士当面的教导,也可以通过基督教出版物,且圣经译本本身的解释性材料也是必要的。这一观念的引入对译名问题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不再执着于一次性翻译的效果,采用不同译名的传教士将会增加互相容忍和接纳的理据和空间。
传教士大会之后,《教务杂志》上差不多每年都会出现译名问题的相关讨论,既有对“神”、“上帝”、“灵”等词的进一步考察,也有具体的解决意见,还有对过往讨论的反思。总体而言,传教士关注更多的不是问题的是非,而是态度的调适,讨论也相对温和冷静,没有前几个阶段那么热烈和情绪化。1919年之后,《教务杂志》上就很少看到译名问题的讨论文章了。而传教士的最后一个汉语圣经译本《官话和合本》在中国基督新教中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一直出版两个版本,“上帝”版和“神”版,“HolySpirit”则翻译成“圣灵”,这是明智的做法,从此以后在没有争议了,这也许可以看做新教传教士对译名问题的最后解决吧。
为什么我们中文版本的和合本圣经的“神版”凡涉及到“神”就出现空一格呢?主要是为了和“上帝版”页数统一,不至于在读经中出现页数不一样。我们在聚会当中也可以听到有的传道人还是使用“上帝版”和合本圣经,这也是对于God领悟和习惯,无碍大局。
笔者历来是倾向于God汉译为上帝。而且在我的文章中和口头传福音时大多是以上帝来出现的,因为我考虑不信的人会把“神”误解为拜偶像的假神。再就也是习惯吧,因为家母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信主的,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说上帝,告诉我们她信上帝、信耶稣,她从来没有说过神。这些都是信仰的枝节问题,也是我们中国基督新教在和合本圣经中具有权威的表述,即上帝和神的圣号都是正确的,实际上在我们主内God是上帝、也是神。如果我们现在还纠结于God是上帝还是神正确,为此争论不休,已经毫无意义了。
“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和合本圣经神版、约翰一书4章16节)“愿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恩典、怜悯、平安给我们,使我们始终生活在真理和爱中!”(现代本圣经约翰二书1章3节)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