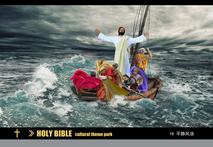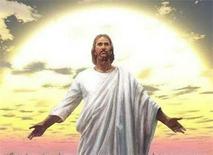《下一站,天国》剧照
在经典电影《下一站,天国》(After Life)静谧而深沉的影像世界里,是枝裕和导演以他一贯的温柔与哲思,构筑了一个介于生死之间的独特空间。影片设定了一个令人沉思的情境: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在死后聚集,共同完成一项庄重而私密的任务——从漫长或短暂的一生中,选出那“最幸福的一个片刻”,让这段记忆成为他们永恒的归宿。他们让死亡的意识重新点燃生命,也让我们看见电影能唤醒人心的力量。
影片开场,我们看到一个个陌生人走进一座破旧的学校。雾中响起铃声,观众也在心里发问: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聚在这里?他们有老有少,看起来毫无共通点,却彼此热络地交谈着。忽然,一个拿着文件夹的女人走进来,歉意地说让大家久等了,然后依次点名,分配房间和辅导员。
接着,我们看到一位年轻男子在教室里迎接一位年长的女士。他微笑着请她坐下,温和地解释他必须按程序确认她知道自己为何而来。
“您昨天去世了,”他说,“请节哀。”那位老太太仍旧带着笑意,平静地回答:“真不好意思。”她的反应让人感到,无论身在何处,她的第一本能仍然是体贴别人,不想让人为难。
从这里起,影片正式带我们走进“来世”。这位老太太的温柔态度,其实是理解这部电影的关键。它谈的不只是“死亡”,甚至也不单是“来世”,而是关于“我们这一生”,当一切结束后,我们会如何回望。
我会选哪段记忆?
导演是枝裕和在访谈中提到,片名《下一站,天国》的日语意思其实是“美好的人生”。显然,他知道1946年那部美国经典《美好人生》(It’s a Wonderful Life),在那部片中,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的男人看见了“如果自己没出生,世界会变成怎样”。
某种意义上,这两部电影都在凝望未来,而非回首过去。但《下一站,天国》并不是那部老片的翻拍,它没有任何闪回镜头,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自己讲述过去的故事。辅导员告诉新来的人:他们的任务,是从自己的一生中选出唯一想带入永恒的记忆。他们有三天时间思考,辅导员会协助他们完成选择。当他们决定好后,工作人员会用电影的方式“重现”那段记忆。影片放映完,他们便会走入来世。
而在选择记忆的对话中,电影展现了最迷人的部分。这部电影让我难以忘怀。不仅因为它让我思考:如果是我,我会选哪段记忆?也因为那些死去的人在离开前被给予的这份“特权”。谁不希望,在世上生命的尽头,能被善意地邀请去回望自己的一生,并在讲述中重新理解它?
渐渐地,我们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为那些说“我没有值得记得的事”的人感到心酸;也被某些记忆深深打动。有一位二战老兵回忆:他们被美军包围,饥饿难耐,盐分匮乏得几乎要死。他以为自己反正活不成了,就向一个美军士兵要根烟,对方真的递给了他。后来,美军还给俘虏们吃了带盐的米饭。“我不想忘记那种善意,”他轻声说。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她几乎不回答辅导员的问题,也许患了失智,但从她平和的神情来看,更像是她选择了沉默。她唯一开口,是走到窗前问:“外面的樱花,会开吗?”这个问题,也正是她灵魂的线索,通往她那段最终会选定的、温柔的记忆。辅导员们有时也会开玩笑——比如那个不停炫耀自己一生中性经历的男人,他的记忆荒诞得让人发笑。然而,当真正面对来访者时,他们从不评判,只是安静倾听。
有个男人讲起自己二十多岁时差点自杀的往事,又谈到那个让他放弃念头的平凡而美好的瞬间。还有一位中年女人,风情万种、情史丰富。她说自己始终是个浪漫的人,却始终没遇到真正的爱。她选择的记忆,是整部电影中最令人心碎的之一,第一次看时,我并不明白,为何她要选“在旅馆房间里等待情人到来的那一刻”。后来我才懂,那片刻虽不起眼,却是她一生中最真切的等待。听懂她的语气与停顿,你就知道,那记忆的悲伤无法言说,却也深具逻辑,因为那是她生命的全部渴望。
不美好的回忆
《下一站,天国》是一部值得反复观看的电影。它的“平淡”,其实是一种极有技巧的叙述。摄影师山崎裕是纪录片出身,坚持用手持摄影机拍摄,这让影片像是在拍真实的人生,而不是虚构的故事。
这种风格也让是枝裕和得以避开那些常见的俗套:柔光、白云、梦幻滤镜、煽情配乐,你不会在这部片里看到任何好莱坞式的“死后世界”。这里没有光彩与奇迹,只有一所斑驳脱漆的旧学校,通往永恒的“中途驿站”。
电影的现实感还有另一层原因。是枝裕和曾说,他拍这部片的灵感,来自他和助手对五百多位老年人进行的访谈,主题是“死亡”。那些故事打动了他,于是他邀请其中一些人直接出演电影。《下一站,天国》中有专业演员,也有十一位普通人,他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延续自己的生命叙事。片中出现的一些日本文化元素,大多可以从语境中理解。比如,一位老妇人讲起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童年记忆,她当时太小,不懂灾难的严重(那场地震与随后的火灾造成十四万人死亡)。她只记得逃到竹林中,与别的孩子玩耍,母亲在火堆上为他们煮饭团。那记忆,竟是欢快的。还有人提到在兄长灵前祈祷,这是神道信仰中常见的习俗。
影片中唯一刺耳的一句台词,出自一个年轻的实习辅导员少女诗织。她警惕、冷漠,对“早死”并不在意,真正让她难过的,是那段没有父亲的成长。当悟郎因为她的态度而发火时,她冷冷地说:“这就是一个女孩没父亲会变成的样子。”这句话让我们窥见一个灵魂的荒漠,当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曾被爱温柔滋养,当记忆的仓库里寻不到一抹温暖的亮色,生命该是何等贫瘠与荒凉。
美善的痕迹
当辅导员和拍摄团队(他们正是《下一站,天国》的真实剧组成员)开始为每个人拍摄他们所选的“记忆场景”时,影片的魅力愈发浓烈。他们剪出纸樱花,爬上梯子,用篮子轻轻洒下;他们齐心协力推着一辆旧巴士,只为重现一位老先生学生时代乘电车的记忆;他们用棉花做成云朵,为那位曾独自驾驶小型飞机的男人营造天空。一切都笨拙而温柔,带着手工气息的诗意。
背景里响起一支业余乐队跑调的军乐,他们吹奏着,带领众人走向礼堂,去观看这些“再现的记忆”。那样的画面拙朴,却叫人动容。然而,在这温柔的重演背后,一条更深的故事线正逐渐浮现。
诗织开始质疑同事们:“我们做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她与望月的关系日渐亲近,也愈发不安,因为她感觉他即将离开,去往真正的“来世”。
在这一周中,一位新到的亡者向望月揭示了一个关乎他自己生命、也关乎他曾爱过的女人的重要秘密。是枝裕和在访谈中提到,他对这个角色有强烈共鸣——那个曾以为“记忆被封存在自己体内”的人,终于明白,他人的记忆,也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望月曾经茫然无依,如今却能说出一句深深打动人心的话:“原来我也曾是别人幸福的一部分,多么奇妙的发现。”最后,望月准备好让自己的记忆被拍摄。那一幕,无论我看多少次,都不免泪流。
这部影片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值得珍藏的生命瞬间,都是上帝赐予的恩典礼物。正如诗篇所言:“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诗39:5)我们有限的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其中散落着这些闪耀着永恒光辉的时刻,那位老兵记忆中的善意,老妇人心中的樱花,这些见证着即使在破碎的世界中,上帝依然留下美善的痕迹。
基督信仰告诉我们,记忆是过去的回响,也是信心的操练。正如以色列人常常数算上帝的作为,我们被邀请在感恩中回顾生命旅程,发现那些平凡的瞬间背后,都有神圣的护理与陪伴。
《下一站,天国》引导我们以敬畏的心,珍惜每一个当下。因为在每个普通的日子裡,其实都隐藏着永恒的种子。电影中的人们,寻找的不只是记忆,他们渴望生命的意义与归属。基督信仰告诉我们,这意义与归属的终极答案,在那位道成肉身,进入人类记忆的耶稣基督身上,祂亲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善的时刻,应许要将我们所有的记忆,在永恒中转化为一首完整的感恩之歌。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